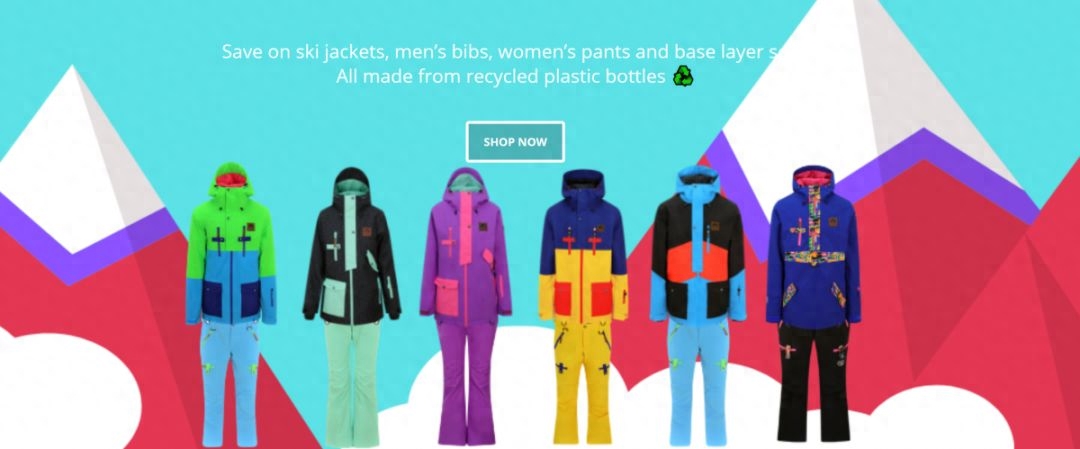曹东勃评《轻文明》︱如何理解和面对一个更“轻”的世界?
今年6月初,我曾受邀参加一场中学生演讲的活动。一位初二女生,现场抽到的题目是“你认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是什么”。只见这个小姑娘气定神闲,沉思片刻,开口道:“我感觉我们人类越来越空虚,无趣,越来越陷入到物质的包围之中,就比如说你们大人”,她指了指坐在台下的我们五个评委,“你们从谈恋爱到走入婚姻,每一步都需要越来越无意义的物质包装和修饰。人们变得更加贪婪,精神上却很虚无”。随即娓娓道来,详加阐发。后生可畏!谈论这个主题的惯性思维,十之八九会落入“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全球治理”之类的俗套之中,她竟答得这样真诚而巧妙!
熟悉后现代主义和法国哲学家的人们,对前面所提小姑娘的问题意识大约不会感到惊讶,那很有几分鲍德里亚反思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意蕴。一个孩子,却能勘破很多成年人身处其中而无法自觉的大问题:如何面对一个更“轻”的世界。
法国的镜像
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所著的《轻文明》,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是过去十余年间,继《超级现代时间》《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永恒的奢侈》几部专著之后,作者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所做的又一次细致扫描。

《轻文明》
对中国来说,地处遥远欧洲的法国一直是具有重要影响和参照意义的神奇存在。百余年来,国人怀着极大好奇,从观察和理解法国的方方面面中观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寻求镜鉴,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中溯源中国经济思想。直至今日,法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其小农传统、法国的文化结构特别是其左翼传统,以及法国的民族多元融合问题、社会治理问题,都与当代中国发展构成某种映射关系。同样,利波维茨基在本书中以法国为例,详细描摹的当代社会思潮的某些新变化,也正在当代中国初露端倪。
用一个绝妙的“轻”字来概括我们所处的时代,利波维茨基并非第一人。米兰·昆德拉在1984年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轻与重的矛盾是所有矛盾中最深奥、最模糊的”。更早的是先知般的尼采,他在二十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就告诉人们,“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只有一个东西是必须拥有的,要么是一种天生的轻的精神,要么是一种由艺术和科学创造出来的轻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是轻生活的神”。
文明当是一种厚重的积淀,何以言轻呢?这里不妨沿《轻文明》的研究路线,不急于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且从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政治六个维度,对“轻”的精神现象做一番考察巡礼。
技术之轻——去物质经济
我记得高中的地理课本在讲到经济地理的部分时,有一个关于“区位”的专题,有一种区位优势就是产品轻薄短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适宜发展空运,不受本地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制约。从经济上看,其结构是由高度依赖重型设备和重化工业逐渐转向以注重大众消费、家庭消费为主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从技术上说,这种轻型化就是一种减量化、微型化、非物质化。正如我们购买笔记本电脑、U盘、iPad等电子设备时,追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轻轻益善”。
尽可能创造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用料更省、阻滞更小的产品,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轻原则深入人心。“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复杂程度、集成水平、技术含量与日俱增,新材料、数字技术、纳米和生物技术的应用,使变轻、变小、去物质化的风潮席卷全球。
不过,去物质化的过程本身,却消耗大量的物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相当巨大,甚至会出现“反弹效应”。比如,制造一个重两克的集成电路需要消耗比最终产品重六百三十倍的辅料,数字技术并没有减少物理运输和某些材料的消耗。在这个意义上,轻与重并非决然对立,而是轻受惠于重,非物质性的光鲜亮丽根本上得益和归功于物质的进一步挖掘——对地球深处的天然材料和矿物的开发,而采矿业本身是重的,甚至是超重的。
经济之轻——消费社会
在至多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履行“给你幸福”的许诺,开启一个个宏大的现代性工程和救赎性计划,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了我们的主流叙事。工业革命以来,在技术与经济的联袂推动下,基本物质需求的束缚逐渐打破,在经济增长为中心、高歌猛进并付出巨大社会代价和阶层分裂之后,人们致力于为生活减速和减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福利社会建立,大众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准配置。信息技术革命则把这一减负的古老事业推到了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大量过剩、商品严重堆积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中物对人的包围,呈现出立体式、全方位的特点。所谓立体式,意味着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存在,一件物品的购买让消费者产生连锁心理反应,使其关联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经济学里把这叫做互补性商品。所谓全方位,意味着一种跨越不同领域的消费航母。正如加载集聚了影院、书城、儿童游乐等功能的商圈,往往要甩出传统的购物一条街模式“几条街”一样,超大规模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掀起了商业经营方式的新浪潮,并逐渐以其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等综合性经营、一站式服务和配套式环境而风靡全球。此外,各类满减、凑单、配售、剁手,多少消费假汝之名,花钱似流水,轻飘而过。
消费社会中的精神需求超越物质需求,文化与符号价值更受重视。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外滩的一个邮筒,因为明星鹿晗合影加持,引来一众粉丝纷纷前来朝拜,以至于有关部门把邮筒“封杀”,粉丝经济是消费社会的当然产物。
市场的拓展及其伟力,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神圣与崇高变得让人感到别扭,世俗化、娱乐化、时尚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各类展览、博览活动日益迎合大众的世俗化意向——车展成了模特的秀场,车却被冷落一旁。本雅明说得透彻:“世界展览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涂脂抹粉。他们创造了使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后台这样一种局面。他们打开了一个幽幻的世界,人们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精神解脱。”政治热情消褪,感官体验升腾,各类带有神圣光环的行业都未能免俗地堕入物的陷阱。

本雅明
消费品不再追求永恒,而是加速折旧、流变、迭代。无怪乎鲍德里亚感叹:“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确,物的消费呈现加速度态势,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睹物思人”,对着一件祖传宝贝,“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消费社会里,人要适应物的更替迭代和新陈代谢。耐用消费品这个概念越来越成为一个滑稽的概念,电视?空调?冰箱?还是汽车?我们对上述哪一个物品的使用超过了十年?在消费社会,一些螳臂当车、顽固对抗这一加速折旧趋势的品牌,比如不识时务、耐摔耐用的诺基亚手机,则遭受了惨烈而不可逆的市场失败,这进一步加速了人对物的追逐运动的速率。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中,消费需求的异质性上升,个体被归类、编码、排序。所有关于消费的话语,都想把消费者塑造成普遍的人,而消费者却期待成为领风气之先的潮人。消费者希望通过商品消费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定制和个性化服务日益成为消费社会的新宠。顾客是“上帝”,“上帝”却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总是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会在追逐时尚、“屡虐屡购”的“剁手”过程中尴尬地发现,所谓时尚,简直是实时更新的风尚,且经常会杀个猝不及防的“回马枪”,令人无所适从。想想前不久有人恶搞的年度四大fashion映射的荒诞现实:洪七公的发型、赵四的西装、光头强的裤子、乾隆爷的黑鞋。正所谓天道好轮回,时尚饶过谁。
消费社会越来越从注重产品自身质量转向重视设计、外观、包装。先人概括得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朴胜于文饰是粗野的,但文饰胜过质朴则是轻浮的。消费社会之轻,正在于此。所以要在月饼盒子的装帧设计上下更大的工夫,买椟还珠在消费社会真的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
生活之轻——瘦身拜物教
生活中人们对轻的追逐的重要表象,是各类冥想、瑜伽、养生、“排毒”大行其道,人们认真地对自己下手,从自己做起,做减法,断舍离——甩掉脂肪的副产品,是甩掉负能量,获得一身轻松的喜悦。
“生于1992”而被迫“步入中年危机”,显然是一个段子。真实的情况是,七〇后甚至都拒绝承认“人到中年”。体态与心态的“轻化”,以瘦为美和装嫩卖萌是同一桩事。现代科技的发展促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人们的寿命延长,而千年来的各种病痛和早夭的奴役则被逐渐摆脱,我们可能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老龄化不再指向一种凄凉衰朽的晚景,人们的肉体将从日常的苦痛中获得解放,无痛苦地度过一生。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这种无痛之轻的状况?医学的普及和对人类的前置介入,可能使人生成为一场巨大的诊疗,人类成为一种“医学人类”——为生存而生活,而非为生活而生存。这看似更轻,实则更重了。
人们同时沉迷于一种客观的轻(清瘦)和主观的轻(轻松)。于是,我们看到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之后,大都出现了健身、瑜伽、太极乃至气功热。讲起来,这些运动方式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但其成为潮流也就是人类摆脱饥馑和匮乏之后不久的事。健身房的功能结构与装饰布局的嬗变,最能反映这种时代之变:起先是“重工业”主导、“重金属”风格,用于力量训练的器械装置都排列在最显要的位置;随后,肌肉的型塑退居其次,相应的器械被边缘化,几乎每一个健身房的核心功能区摆放的都是成排的跑步机、骑马机,“重”的力量训练让位于“轻”的有氧运动;健身房终于从最初的健美爱好者甚或运动员的训练场所,转变为一种老少咸宜、零基础起步的“室内瘦身广场舞”地带。
从保健只是作为特定人群专享的一种泛医疗待遇或福利,发展到人人可言“保健”,可言养生,直至“大保健”成了一种带有调侃讽刺意味的特定语词、黑话;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再到全民健身,以至于发展到大爷大妈和自己的孙辈争夺篮球场,轻时代全面降临。
反讽的是,这种对“轻”的全民追求,恰恰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产物,强调它,只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远。这种修身养性的自恋式狂热背后,不过是这个以绩效、业绩为中心的社会里,一条条劳碌命不自觉的日常反抗罢了。而这种反抗的虚假和脆弱性,也一如消费社会中的其他种种,很快湮没在数字的表象之中:明明加班“累成狗”,却倔强地发一张蓝天白云的正能量美图到朋友圈,彰显一种淡泊宁静“我很好”的状态;围绕“每天一万步”的目标“比学赶帮超”,修身养性成了廉价的行动;无论墙上挂多少张《好了歌》《莫生气》,动怒之际瞄都不会瞄一眼。
瘦的拜物教与轻的拜物教合二为一,一种现代的野心日渐升腾:寻求命运打击不到的地方,亲手雕琢、控制、维护自己的身体。于是,多少明星大腕梦寐以求“逆生长”、“飞升上神”;于是,七十岁的希拉里老太太只因跌了一跤就被人百般质疑。减轻身体负担的举动反而增加了生活的负担,不能有效控制身体的人被认为缺乏自律的品质,身形就这样与人品悄然挂钩。
文化之轻——百无聊赖
轻文明意味着一切,唯独不代表轻松的生活。如果说前现代的艰苦卓绝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现代的空虚无聊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当资本主义精神渐趋宵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想法就趁机填补了价值的真空。在精神虚无的时代依然诉诸物质资源,只能是黔驴技穷,不仅荒诞,而且自残。
告别总体性社会的宏大叙事,放逐于小时代里的小确幸,乃至寄情于消费,终归于空虚、无聊、虚无、犬儒。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类似的精神现象只可能出现在少数贵族身上,并最终只会在其中一部分人身上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更常见的则是“病毒携带者”。如今,这个问题则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可笑的“何不食肉糜”的问题。随着大部分人衣食无忧后,丰裕社会、消费社会这一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将引发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以及这一精神领域“富贵病”的迅速扩散。
时代主题既已转为产能过剩之后的经济危机,人们的焦虑所在也就必然转向物质过载之下的精神重荷。人们不能不追问:消费主义为世界减负,靠谱吗?以物质主义、好生活的世俗目标作为激励,就不免要面对如下三个问题:其一,这种穿了红舞鞋一般永不停歇的发展和改变究竟何以完成?其二,人类如何来适应这种快速发展?其三,商人能否描摹出精神世界的理想化替代性图景?
塞托夫斯基也曾发问:“一切(生理)需求都满足后,一切不适都消除后,机体将做什么?过去的回答是什么都不做,现在已经普遍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烦躁是不可消除的,烦躁是伟大的杀手。”鲍曼则调侃现代社会的精神特质:“假如你心情低落,那就吃。”

鲍曼
吃货不可能拯救世界,消费也不可能排遣孤独。看看那些每天早晚马路上的“晨跑族”,他们的步伐多么轻盈!不,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耳朵上挂着耳机,胳膊上绑着手机。我更愿意比附“互联网+”称这一奇景为“耳机+”现象,无论跑步、散步、健身、购物都要加上一副耳机。在消遣的时候总要输入一些元素,否则便不觉得是在消遣,甚至觉得在浪费时间、虚耗生命。这到底是消遣还是忙碌?轻松还是沉重?
趣味的缺失是更为可怕的,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脱离低级趣味”问题,而是趣味的品鉴本身已经成了问题。所以,当要送人礼物的时候,只得上网求助各类商城里专门贩卖“金点子”“鬼主意”的商铺,假手于他人为自己做选择,丧失了创意和思考的能力。物品的泛滥与趋同,使得我们无所适从,不知如何选择,既不知如何犒劳自己,也不懂如何惊喜他人。这才有各种趣味商店、创意礼品,乃至各种恶趣味、重口味。

弗洛姆
如果深究这一紧随丰裕之后的空虚源出何处,弗洛姆的洞见不妨一观。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人性是人的动物性降到最低点的产物。作为动物,人类是以失败者的身份一路溃败而来的。倘若人类当初是成功的猴子,那他应该继续在树上生活。可见,人类在其猴子时期,就是乏善可陈的loser。他被赶下树来,另谋生路,希望一雪前耻,做一个合格的草原动物。可是,狮子老虎豹子怎么可能会容得下这个新来的废物!于是,人类的祖先继续疲于奔命地逃向平原,逃到没有人,不,是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打搅他们、欺侮他们的地方,渐渐地过起了人类早期的采摘、狩猎,以至农耕的生活,形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范式。这一路溃逃中,每当他想利用动物的本能试图随遇而安地适应一下的时候,他都被第一时间赶出了现场。他简直成为了动物界的耻辱,一切动物都羞与为伍。当他不再谋求适应,而是在走投无路之际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创造活动时,人类诞生了。人类一路进化而来,也是一路退化而来,这一路失败的结果却是:不成功,变成人。
离开了伊甸园、舒适堡,人与自然之间不再亲密无间,主客的二分的改造世界之路艰险异常。选择了这条道路,不仅要探索未知的一切,还要寻找自身的意义。人对物质的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仍会产生新的不满。所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物质需要满足易,文化需要满足难。人是精神的动物,文化与精神方面的欲壑难填。如果人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可高枕无忧的话,中央电视台街头采访到处提问那句“你幸福吗”,得到的应该是整齐划一的肯定答案。显然,温饱的解决并不是问题的结束,恰恰相反,人的问题刚刚由此开始。
伦理之轻——家庭的松动
家庭关系这一传统中具有压舱石效应的重量级关系,也正在不堪重负,出现松动的迹象。人们渴望活得自由潇洒,摆脱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包括家庭。由此,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出现了全面的动摇。作为轴心的夫妻关系,其基本的维系条件由“忠诚”悄然撤换为“尊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解放”运动的触角伸向家庭。
追求风流的生活模式,并非某个时代所特有。启蒙运动时期,玩乐、猎艳甚至成了所谓上流社会的时尚,不妨称之为“放荡之轻”。不过,当忠诚被宣布为可笑之物,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就被等同于一场基于策略的社交游戏。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轻,看似放浪形骸,实则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求表达的优雅、情感的伪装、勾引行动的完整。而另一种“酷之轻”则要求完全破除定势,无拘无束。“酷”貌似是个已经过于老土的词,但它的流行实际上不超过半个世纪,在中国甚至还不到三十年。
近几十年来,婚姻和家庭制度受到重重包围和挑战。有侧面的挖墙脚——试婚、结婚、离婚、再婚、复婚的反复“试错”,人们对多线程恋情、脚踏两只船变得睁只眼闭只眼。神圣的殿堂似乎成了摆设,不渝的承诺变为美丽的谎言。也不乏来自正面的进攻——丁克主义乃至不婚主义异军突起,“婚活时代”这个来自日本的术语,形象地表达了一种越俎代庖的普遍焦虑,无论是父母替子女相亲、还是组织机构过问年轻人的婚恋问题,恰都说明家庭已由一种温馨之所变为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沉重负担。日本的大前研一把这种状态描绘为“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愿背负风险、承担责任,同时也对出人头地、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等世俗欲望一并彻底心如死灰。“宅”文化、“丧”文化、“啃老”现象,也就都不难理解了。
即便是光棍节这样一个略带沉重和自嘲的节日,自其创生之日即已脱离本意,逐渐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消费体验和狂欢庆典。何以解忧?唯有消费。所有的愁绪,所有的差异,都被夷平在消费的狂热之中。
不过,家庭也并没有被轻易打垮。对忠诚的信念确实在弱化,也许人们对不忠的容忍也在增加。但一经出现明星艺人的蜚短流长,人们总是“舆论一律”地展示自己义愤填膺捍卫家庭价值的道义感,而结果也必定要以肇事者的低头认错、公开道歉告终。这种言行的有趣背离,也是轻婚姻时代的典型特征。
家庭关系的松动只是道德约束日渐软化、轻化和各领域全面退缩的一支先遣力量。一旦家庭中的责任底线不能坚守,其他领域的道德滑坡或相对主义必然出现。价值理性自身开始退缩,承认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相对于某种有限的目的和视角而言的,不存在某种规范性论断优于其他论断的那种立场——“怎么都行”。发展至极端,便出现了否定任何终极价值和意义,因而否定任何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的客观准则的犬儒主义。在市场深度嵌入的现时代,犬儒主义表现出出离世界、驳难价值、敌对文化的倾向,它拒绝反身自顾,它践行玩世不恭——因为在其看来,这世界本就不值得“恭”——“认真你就输了”。“拒绝崇高”“告别理想”“活在当下”成为颓废、卸责、袖手旁观甚至见死不救的普遍说辞,道德在不经意间被高高举起后,又轻轻地放下了。
政治之轻——景观政治
轻的革命绝不只限于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诸端,它也成功地改变了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运作。如果说消费社会是一种物体系包围和营建的景观社会,那么其在政治上的镜像则是建构了一种景观政治。
政治决断为迎合民意的情绪表态所取代,政治理性为煽动民情的激烈言辞和极端立场所取代,政治的宏大叙事和严肃主题为庸常化的细碎琐事与政客的演技化、亲民化、生活化所取代。自电视出现后,媒体的发展日益将政治的场所装扮为政治的舞台和政客的秀场。政治上的轻革命,也就是为政治减负。政治家走下神坛,民众不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英主和父亲般的人物,而是可以撸起袖子与民同乐、打成一片的兄弟与伙伴。当然,这种祛魅的本身产生了另一种赋魅的效果。
轻政治围绕态度做文章。所谓民意调查,主要是对态度的侦测,而态度本身是流动的。基于简单的表态游戏,可能做出错误的、不可挽回的政治决断。宏大叙事的信仰终结和进步主义的幻灭,使政治成为一种表态政治,民主成为一种影像民主——直播、金句、图像取代了仪式、争论和观点,政治的语言变得轻飘无力。
政治下沉,市场升腾。对金融资本逻辑的膜拜,使经济之重成功掩盖了政治之轻。娱乐化,则让政治变为《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那样一地鸡毛的官僚琐事。人们对此毫无兴趣,抑或只钟情于纸牌屋里权力的游戏。政治何止被轻化、八卦化,更被黑化,这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其敬而远之。

《是,首相》

《纸牌屋》
传统中只能居于帷幕之后的运筹博弈、理性狡计,被全盘搬到台前。现实主义,甚至进攻性现实主义,大有取代政治正确的理想主义之势。选民索性谁都不信,全靠自己,他们也更加倾向于保持观望,直至最后再做出决定。这样一个去政治化、去政党化的“战略型选民”时代,固然是个体化得百花齐放,却也着实带来了更大的政治不确定。
民众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不信任,来自于面对当下经济社会困局时的两个深层失望:一是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创世雄心和理想信念走向破灭,二是那种西西弗斯式的脆弱无助时时涌上心头。这些选民没有整体性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方案,也没有掌权的意图,旨在一事一议,就事论事,专注于局部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只是相对于传统的政党政治,它是一种轻型政治,更加灵便,更有效率,但也更捉摸不定。
政治基础设施已铺就并运行良好,人们的各种反对意见也并不旨在推翻这套制度。但这种温和而轻民主的政体,确实无法阻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煽动和洗脑,根本的问题依然是,这个轻的世界无法为衣食无忧的人们提供存在的意义、集体的身份认同、结构性的定位和自我评价。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与身份区隔,各种鄙视链条横空出世、应接不暇。分裂机制的存在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来说,整个社会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对于福利、消费、娱乐的追求,人同此心。信息壁垒的破除,也让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模仿变得非常简单。各种保障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全覆盖,其次才是保障的程度。这是因为,有没有,是一个政治权利问题;有多少,是一个经济分配问题。重度不平等状态下的轻政治,仍然无法褫夺人们追求幸福、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更“轻”的世界?行动的轻盈并不能驱逐内心的沉重,技术的进步也无法解除生活的沉重。利波维茨基提出:“与快感有关的局部的‘轻’正在蔓延,而由喜悦产生的整体的‘轻’最好的情况也仅仅是停滞不前。”这是否意味着要对轻文明大加挞伐?不,轻本身并不消极,甚至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没有必要局限于生活方式的浅薄、轻佻、享乐主义来理解。
小时代本身并不让人厌恶,小确幸也很合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现代潮流,但当这种轻飘氛围的膨胀、扩张、渗透、通约一切领域,侵入生活并试图扼杀生活中各种丰富可能性,问题便产生了,人们的思考、创造、伦理责任、政治责任会被卸载一空。真正的“轻”,是尼采所言“带着镣铐起舞”的那种心态,在对抗整个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守护生命的高洁与轻灵。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44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