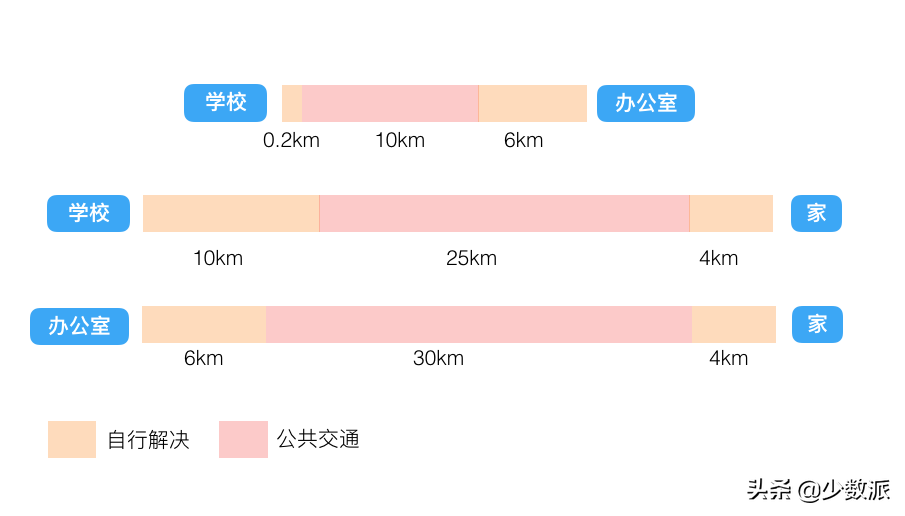登顶乞力马扎罗
乞力马扎罗山有两座主峰,即基博峰和马文齐峰,两座山峰之间由一座鞍状的山峰相连。基博峰是两峰中较高的,高达 19341 英尺(约合5895 米);而马文齐峰则差不多矮了半英里(约合 0.8 千米),有 16896 英尺(约合 5150 米)高。中间的鞍状山峰则有 16000 英尺(约合 4877 米)左右高。整座乞力马扎罗山占地 995 平方英里(约合 2577 平方千米)。

△ 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最高的山峰,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山峰。
我依然沉浸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兴奋中。最后一批象尾毛手镯卖了个好价钱,随后我回到自家农场的车库。我把摩托车拆卸开,把零部件摆在地上,小心地给零件清理和上油,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好,然后带到南基南戈普的当地修理厂,喷涂上新油漆,和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我把摩托车擦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它看起来就跟全新的没什么区别。
6 个月前走出摩托车商店的时候,我这辆摩托车的里程表显示约 500 英里(约合 805 千米)。而现在,它已经接近 7000 英里(约合 11265 千米)了。倘若我从未去过开普敦,那么它应该在 1000 英里(约合 1609 千米)左右。于是我把里程表上的玻璃罩撬开,将里面的数字往回改到 1497 英里(约合 2409 千米)。

然后,我骑着摩托车到内罗毕的里弗尔路(River Road),销售商索汉·辛格(Sohan Singh)就站在销售点边上。他是一个长相英俊、巧舌如簧的锡克教徒,头戴黑色的头巾,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下身穿着城市骑行裤,外面套着一件及膝长的干净的白色工作服。“啊,杰弗里先生!很久都没有见到你了,你都在忙些什么呢?”
“这 6 个月来我一直在野外旅行。”
“杰弗里,你的摩托车看起来车况很好。”
“我很高兴你这样说,索汉,因为我正在考虑让你把它回购过去呢。”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摩托车卖回给我呢,杰弗里先生?”
“我需要把它卖掉,因为父亲仓促地通知我,让我收拾好行李,就送我到桑德赫斯特。那儿可没办法留着一辆摩托车。几周后我就要出发了,所以想尽快把它卖掉。”
“我明白了。”索汉·辛格说,“你的摩托车骑了多少英里了,杰弗里先生?”
“大约有 1500 英里(约合 2414 千米)。”
“1500 英里!你一路骑到哪里去了,不会是开罗吧?让我想想……”
他的手指在上唇上连续敲打着,然后说,“告诉你,杰弗里。因为我非常欣赏你这个人,所以我给你摩托车原价的四分之一。”
“索汉·辛格,四分之一?没门儿。”我们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直到他答应付我原价的 70%。
一周后,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骑着摩托车到开普敦的文章,索汉·辛格立刻给我家打电话。“杰弗里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好朋友?”他喊道,“你难道不知道我读了你的报道了吗?请立即回来,我们要讨论一下你的退款!”
“索汉,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你那里买了三辆摩托车了。因为我急切需要,所以你每次都卖得很贵。在这场较量中,你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我不打算退钱给你。”
几天后,当我与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领队斯特劳德(Stroud)少校见面时,我的这种自信心又派上了用场。斯特劳德少校有点瘸,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以一种冰冷无情的口气向我们作讲解,那是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他比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都年长几十岁,而他身上那种热情与专注,让我们对他笃信不疑。
我们一共 20 人,乘坐一辆小巴士从内罗毕出发。斯特劳德少校坐在前排,整个上午我们一路上都没说话。“谁知道‘乞力马扎罗’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手:“我想我知道。”
“肯特?”
“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就是‘旅行者望而兴叹’。”
“没错。它源于坦桑尼亚当地的一种方言查加语(Chagga),原意是山是如此之大,任何想要尝试翻过它的人都应该受到警告。大多数人从坦桑尼亚一侧攀爬此山,但是我们要走的路线更为艰难——将从肯尼亚一侧征服它。”
“这是为什么?”一个人问。
“因为坦桑尼亚一侧的斜坡上有花豹和猴子,会把我们撕成碎片!”另一个人高声说道。
我和斯特劳德少校一样,都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不过,我发现少校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个传言。

我们在位于肯尼亚洛伊托济托克(Loitokitok)里一个极其破旧的小镇下了车,这里位于内罗毕以南,车程三个小时,毗邻坦桑尼亚边境,就在乞力马扎罗山的低矮山脊之间。“就是这儿了。”斯特劳德少校说,“远处那座小山的另一边,就是我们未来两周的家。”站在山脚,人们怀着敬畏之心仰望这座高山:晨光与浓雾交织在一起,在一片粉色与褐色混杂的黏土色调中,渐渐显露出山脊。树木构成了远景,美丽动人,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

斯特劳德少校说,为了训练,我们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跑 5 英里(约合 8 千米),运动后回到营地,脱下衣服,跳入由天然瀑布形成的水池中——“温度正好在冰点之上,完全天然,”他说,“必须让你们尽快适应。”在训练之初,我们把时间都花在能够增强力量和耐力的锻炼和运动上。因为正如领队提醒我们的那样,一旦你身处乞力马扎罗山之中,想打退堂鼓就没那么容易了。
少校把我们两两配对,我们彼此将要在这些低坡上度过三天,一起用叶片巨大的蕨类植物和防水帆布建造栖身之所。我的搭档名叫费斯图斯(Festus),是个精瘦但肌肉发达的非洲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名肯尼亚的拳击冠军。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约合 1.86 米),浑身上下都显露出真诚。
斯特劳德少校把野战口粮按小份一一分发,每个人都有罐装食品、咖啡、饼干和三根木质火柴。“要是你把火柴弄丢或弄湿了,”他说,“就只能吃冷冰冰的罐装早餐,没有咖啡,也没有茶。”
开始上山之前,我给费斯图斯打了个手势,让他到我的帐篷里来。“把你的火柴给我。”我低声说。他毫不迟疑地从包里掏出火柴,并递给我。
我用刀片把每根火柴纵向切成两半,再用玻璃纸包好,放回军粮袋。
“12根火柴。”费斯图斯笑着说。
“没错,”我向他保证,“不是六根。”我拉上背包的拉链,开始往山上进发。

为了培养耐力,攀登计划分成了四个部分,一共是四周时间。第一周征服鞍形山峰。斯特劳德少校带着我们在四天的时间里上山又下山。他那永不疲倦的精力与超强的登山导航能力令我万分震惊。“这一路最大的敌人不是山,也不是周围恶劣的条件,”他解释道,“而是这些低矮山坡上的大象和水牛。最好都小心一点。大家都知道,如果与一只水牛面对面的话,你要用枪打它哪里?”
“两眼之间!”一个家伙喊道。
“你为什么不跟紧我,柯林斯?”斯特劳德少校说,“这可能会救你一命。”
我暗自笑了起来,脸上却不露声色……
征服了鞍形山峰之后的那一周,我们又攀登了一次。现在,我们将直接攀登马文齐峰。“由于高原反应和脱水,在这次攀登中,我们的团队人数将会减少。”斯特劳德少校说,“如果你没能成功登顶,那么就只能在我们回来的时候见到我们了。”

从鞍形山峰到马文齐峰,全程 1500 英尺(约合 457.2 米),覆盖着火山灰、碎石和雪——没有一点绿色植物。我向前迈一步,又倒退三步,脚和脚踝便裹着一片泥雪掺杂的污泞。尽管年岁更长、腿脚不便,斯特劳德少校却快步如飞。我追随着他的足迹,尽全力跟紧他——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也因此让我的头脑从攀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并且,每当我看到他喝水,我也会从我的水壶中啜饮一口。
十几个成功登顶的人在山上气喘吁吁。我们爬了整整一上午,几乎一步不停,更无心欣赏阳光照耀下的基博峰全景,才最终到达那里。“这里的空气比你以往呼吸到的都要干净。”斯特劳德少校一边转身下山,一边告诉我们,“在这种纯度的空气里,呼吸系统会变得疲劳不堪。下山的时候大家悠着点。”

△ 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有三个火山口:基博峰(Kibo)、马文齐峰(Mawenzi)和希拉峰(Shira)。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们再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但这次是靠近基博峰火山口的边缘,那里也被称作吉尔曼峰(Gilman’s Point)。我恨死了背包,它只有 40 磅(约合 18 千克)重,但因山上氧气不足,背着感觉像足足有 200 磅(约合 91 千克)重。我一直低着头,盯着面前的地面,好让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东西上面——刹那之间,前方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片冰崖的景观。它异常陡峭,像是一个巨大的透明蓝色阴影悬在头上。“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已经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一般指到了吉尔曼峰。”斯特劳德少校喊着,声音中夹杂着粗重的呼吸声,“但是,要说真正地攀到了这座山——这座基博峰的顶点,你还得挣扎着走过大半个火山口,绕过这里的边缘,到达北部边缘的高处。那就是德皇威廉峰(Kaiser Wilhelm Spitze)。”
“我们下周要爬上去吗?”一位同伴问道。
“我会爬上去的,”斯特劳德少校说,“但是你们中间没几个人会和我一起爬到顶峰。”
正如少校所言,在下一个星期,我们就往德皇威廉峰进发。在我身后,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现在要是有个搬运工就好了。”这还没爬多久呢!我很庆幸把背包留下了,身上只带了一点吃的和两壶水。这绝对是正确的决定。
我们一次最多走三步就要停下来喘气。当我努力呼吸时,极目所至,地面上的雪花如彩虹般闪闪发光,仿佛一块块宝石。我凝视着仍在远处的更高的山峰,仿佛看到一块巨大的蛋糕上整个都堆满了厚厚的白色糖霜。

每一次回头,我都看到队伍的人数在变少。费斯图斯还没有落下,但现在他已经举步维艰了。“疲劳就是考验。”斯特劳德少校咆哮着说,甚至他也显得痛苦万分。经过八个小时连续不断的攀登之后,我们终于接近了顶峰。我回头看着那些危险的山峰边缘,眼前景象让我大为惊讶:在下方,一大片白云仿佛铺起了一个大蹦床,而我们则好像身处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一样。如果现在能跳伞,一定非常好玩。
最终,我们只有六个人爬上了真正的顶峰。唯一的遗憾就是费斯图斯没有在我们中间。
自我们见到他以来,斯特劳德少校第一次以一种庆祝的口吻,催促我们去观看火山口的内部:它是如此雄奇壮观,巨大的冰川在其中就像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冰之岛屿。然后,我们一起靠近那块有名的木牌,上面刻着用黄色油漆涂成的文字:
祝贺你你现在站在德皇威廉峰之上非洲最高点19341 英尺(约合 5895 米)

我们中间响起一阵胜利的欢呼,夹杂着口哨声和沉重的深呼吸声,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成就感中。眼前的景色除了天空就是无垠的空间。它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折服人心。
我们发出的每一点声音都会在身体、大地和空气之间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相互作用。在这里,在大自然中,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生命合而为一。
除了这般壮观的景色,更复何求?成就感之外,我们更体会到了一种安宁与纯粹、一种绝对的自由。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高峰,就像站在世界的屋脊上一样。我转向斯特劳德少校,问道:“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可以在本子上签名了,对吗?”
“是的,肯特,你可以。”
我转身走向祝贺木牌,它的底部有个铁盒子。
“不过要再爬一次以后才行。”
我停下了脚步。
“感到吃惊吗,肯特?”
“不吃惊,先生。”
“好样的。这样做,你的名字将在这里永存。好了,先生们,”他说,“我们下山吧。”

△ 登顶庆祝
我们合成一队,开始下山。我的足迹一路向下,压过积雪,嘎吱作响。休息了三天时间,斯特劳德少校就召集我们第二次登顶基博峰。这一次更加容易。我们身体状况良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也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一次费斯图斯也爬上了山顶。
最后,斯特劳德少校让我在那个本子上签了名。现在,德皇威廉峰也有了我的一席之地。
桑德赫斯特,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源 |《华丽的冒险——环球奢游帝国开创者杰弗里·肯特回忆录》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496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