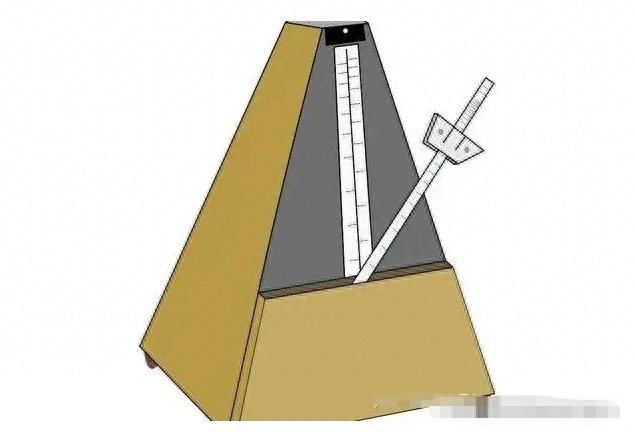两千年前,它已是中国好声音,现在却成为人人皆可上手的启蒙乐器
摘要:非遗最好的保护方式是让它进入生活。
历史古籍对呜嘟的文字记载不多,《嘉鱼县志》曾记载"泥呜嘟,古称吴嘟,为三国东吴时簰洲牧童所创",随后流传于长江中下游。

千年来,这种乐器虽带了27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气质,却始终因音域受限(只能吹奏10个音阶)、表现力差而长期不被重视。
发展至今,吹呜嘟、做呜嘟之人,寥寥无几,能够专心做传统陶呜嘟之人,更是寥若晨星。
唯有热爱,才能付出时间与气力。
制呜嘟人杨德云,他不是从小学呜嘟、制呜嘟之人,只是偶有一次听到这远古之音,自此几十年,痴迷于此,心慕手追。

从自小喜欢音乐到成为呜嘟非遗传承人,他从研读历史、深研技艺,再到拜访名师,每一步,都走的尽心竭力,他有一辈子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心气,更有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东西的倔强。
杨德云老先生对待呜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份温厚的喜爱,他认为呜嘟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自己童年时的玩伴,也是自己愿意坚守并发扬光大的事业。

于是,很多人制呜嘟人向他请教,呜嘟色如何烧的古朴,音色如何变得圆润、浑厚,他回:"土净、音净、人心净"。
真的喜欢,真正的真,无有不成。
杨德云老先生的工作室偏居一隅,架子上整齐摆放着形色不一的呜嘟,把玩起来,带着些许温度,更带着些许对泥土的敬意。

老先生在谈及成为呜嘟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有着轻描淡写的洒脱,这种洒脱,正如他本人对生活与人生的一切经历一般,所有悲苦离奇都消散泯灭在淡然的笑意中,就好像几十年的揉土岁月,所有的脾气都揉进了陶土里、熔进了窑火中。
经过多年的研制改革,杨德云老先生对呜嘟进行了改善,将单吹呜嘟改成双吹和声呜嘟,一个乐器两个声部可以随意编排,以不同的排列组合的方法,呈现出"无数"种不同的声音,大大扩宽了呜嘟的音域,从原来的三五个音阶扩展为十三个音阶,甚至二十个音阶以上,并有低音、中音、高音多种类的呜嘟,这在当今乐器中都是实属罕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杨德云呜嘟系列。

不用借助过多工具,只需一双手,就能融入对自然的崇尚。泥土有各种表情 、各种语言 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与表达 ,只有当心手和泥三者合一的时候作品才能像山川与河流般自然和谐。

他所制作的和声呜嘟已在1997年获得国家专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能演奏和音的土类乐器。
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最终制作成型,达到音色上的和谐,却非常难,从土到泥,再从坯到音色纯正的呜嘟,工序制作起来很是耗时。其中艰辛周折几多,每每提及,杨德云老先生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慢慢研究琢磨"就带过了当中的波折。

制模:将陶土放进石膏制成的两个模子里,在两手之间反复的拍和握,待揉出呜嘟的样子后,再将两半模子合在一起,再次打开模子时,看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呜嘟。

打孔:也叫歌口,是呜嘟制作呜嘟的关键步骤。

定音阶:调音是保障呜嘟能吹出优美音色的重要环节。
抛光:抛光后可以使呜嘟表面更光滑。

烧制:最后入窑烧制,是水、土、火的交融,成器不成器,付出手艺和技艺,仍要看天意。如此这般种种极致追求,万古之音陶呜嘟方能形成。
非遗最好的保护方式是让它进入生活。
泥捏的东西,发的是土声,是地气。现代文明产生下的种种新式乐器,可以演奏华丽的东西,但绝没有呜嘟那样独守着一份自然和朴实。
呜嘟不似其它乐器,它发音圆润,气声小,穿透力强(传得远),在快速、变调、和音(连体呜嘟)等方面都能较好表现,上手也非常的方便,人人皆可学习。

追求传承的理念不改,保留远古之音的初衷不变。"守护"两个字,道出了一种传统生存的方式。既然是传统,必然有其历史的部分,唯有以尊重和匠人一般的执著,才能让传统中深远而严肃的一面保存下来。但若只是守护,传统便如同博物馆玻璃罩后面的展品,同生活相隔,非遗最好的保护方式是让它进入生活。
每个人不需要当艺术家,但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被艺术环境浸染的环境,艺术是塑造孩子心灵的良心工程,杨德云老先生说他希望把呜嘟带进校园,带给更多的人。

时至今日,或许呜嘟的音色特质不会成为大众喜爱的乐器,成为演奏舞台的常客,但懂它之人必是极喜欢的,那些深爱古乐的音乐家,吹它;那些深爱陶呜嘟的手艺人,制它;还有有清风明月夜那些聆听呜嘟的人享受远古淳朴的音色,疏解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爱恨离别。
它跨越2700余年的时空与我们对话,再现我们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让我们在苍凉和温厚的洗礼中,看清真实的自己。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64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