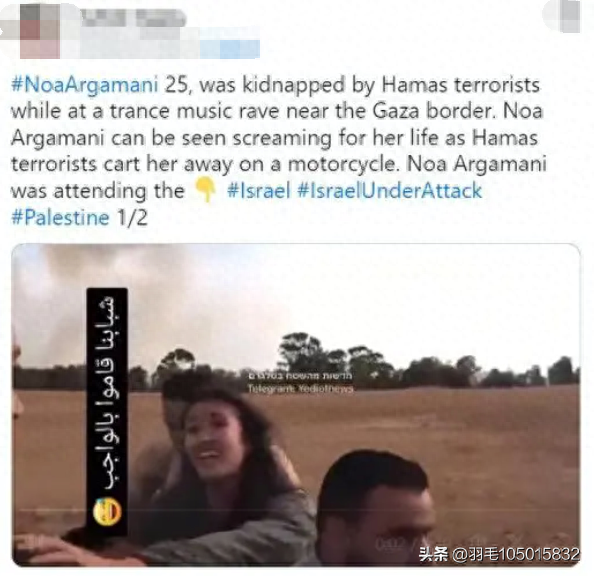1810年非洲女孩身材奇特,被骗欧洲当动物展览,去世192年才安葬
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02年8月9日,非洲开普顿城以东470英里远的盖蒙图谷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葬礼。
人们接过一件被誉为“非洲维纳斯”的“艺术品”,将她放在铺满了鲜花的棺木里,轻轻唱起安慰亡灵的歌谣。

阔别近200年,无数南非人民因她的回归热泪盈眶,连时任总理的姆贝基也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她的葬礼。
这件“艺术品”是一个来自南非科伊桑部落,名字叫做萨拉·巴特曼的活生生的年轻妇女。
相比于艺术,萨拉·巴特曼的存在,更像是在向世人揭露一段黑暗而惨痛的历史——那段浸满了非洲人民血泪的侵略史。
随着她入土为安的这一幕传播向世界,非洲人民心中的愤慨却丝毫不减。
历史掩埋以后,萨拉·巴特曼就能够在故土上安息了吗?

通往自由的谎言
1810年,21岁的萨拉·巴特曼跟随队伍一起,前往当时强大又富丽堂皇的欧洲。
黑人亨德里克·塞萨尔告诉她,去了欧洲她就能摆脱奴隶身份的束缚,成为一个自由人。
他用诱人的语调,向巴特曼描述了去往欧洲后,即将过上的幸福的生活。
巴特曼的丈夫被从荷兰来的殖民者杀死了。她原本是奴隶主夫人的奶妈,因为丈夫的死去变成了新的奴隶,只能看着奴隶主的脸色过活。

如今她在南非了无牵挂,被这个黑人所描述的场景所吸引。别的不说,摆脱奴隶的身份这件事便已经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她随船队来到了英国的首都伦敦。这里充斥着新世界的机遇和美好,但巴特曼的梦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覆灭。
见到她的第一眼,亨德里克便被她极其特别的腰臀比震惊,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女孩会成为他的摇钱树。
这一年,英国的辉格党正准备上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领袖格伦维尔拥有一个肥硕的大屁股。
追捧的人称赞领袖的大屁股,而反对党则用尽了讽刺的方式,极力诋毁格伦维尔。

在两党的斗争中,大屁股成了极为流行又极具侮辱意味的标志,变成了上至英国贵族,下至平民的狂欢。
但和欧洲的猎奇所不同的是,在科伊桑部落里,丰臀代表着女性的健美和风采。少女们在青春期里发育良好,身上的大部分脂肪都被堆积在了臀部,巴特曼在年轻的女性中更为出众。
亚历山大·克洛普和亨德里克·塞萨尔用花言巧语,把这个年轻的科伊桑妇人诱骗到欧洲,想在她身上榨取利益和价值。
对于年轻的巴特曼来说,这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
她被哄骗着签下一条条令人乍舌的不平等契约,表明她的表演是在履行职工的义务,一切的行为都是自愿。

“戴上镣铐吧,女士”,亨德里克拿着一条粗大的锁链靠近:
“这里的人都喜欢这种表演方式,你带着它起舞的样子一定美丽极了。”
“我真的能靠自己赚钱,然后获得自由身?”巴特曼怀着当模特的梦想带上了锁链,不确定地问对方。
同为黑人的亨德里克打量着她,满意得点了点头:
“当然,你可是我弟弟庄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美人,如果你都不能赚钱,那其他人更不要想了。”

他拍了拍身后的笼子,对巴特曼说:“进来吧,你不用走路,我们送你过去。”
巴特曼低下头,听话地钻进笼子,被一晃一晃地运往了广场上。
几经辗转的“商品”
如两个商人所料,巴特曼在广场上一出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伦敦街头卖艺者不在少数,但过往的行人,都纷纷为这个呆在笼子里的女人驻足。
巴特曼像是一件让人爱不释手的珍奇一样,被挂上了珍宝和羽毛,披上带有非洲特色的衣袍。
她被关在笼子里唱歌,又拿起非洲的传统乐器演奏,动人的歌声让喜欢稀奇事物的欧洲人眼前一亮。

但这并不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在路过的伦敦人眼里,相比于其他卖艺者,被关在笼子里的巴特曼更像是一只格外通人性的“动物”。
一些政客伺机而动,皱着眉头想要从她的身上做文章。终于,他们找到了巴特曼身上值得宣传的点:
这个有着黝黑皮肤和丰满身材的非洲人,她的臀部居然要比领袖格伦维尔还要惊人!
上流贵族和底层民众蜂拥而至,把她的周围围得水泄不通,纷纷想要上前一睹这个从非洲来的“稀奇品”。

她被勒令跳舞、下蹲,甚至弯腰。她被剥去了大部分衣物,裸露着站在笼子里。
有好事者将她画成了一部讽刺漫画,贴在大街小巷的街头,借此来和领袖格伦维尔做对比。
此时的欧洲正在开启工业革命,他们是海上霸主,是日不落帝国。在他们眼里,非洲不过是一片未经开化的土地,非洲人民也不过是一群奴隶和牲畜。
将巴特曼和领袖对比,不过是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成一个笑话,用她作为人的尊严去侮辱自己不喜欢的政客。
这让巴特曼的境遇更加糟糕,她成了疯狂者肆意侮辱和嘲讽的对象。

她也想抗争,向周围围观的群众求救,但无人在意从这个“观赏品”口中说出的话语。
也有人想要拯救她,非洲协会的废奴主义者站了出来。
他们以1807年在《奴隶贸易法案》中被废除的奴隶贸易为依据,驳斥了这种荒诞不经的表演,请求释放巴特曼,并调查清楚她和带她来到欧洲的两人之间的关系。
让人遗憾的是,这场拯救行动并没有让巴特曼获救。由于语言不通和人身控制,她只能被迫向法官表明,她所有的表演行为都是自己的意愿。并且,她也从表演中获得了一小部分的报酬。

人们不会去辨析她话中的真伪,也并不在意巴特曼是否就是应该被拯救的奴隶,君子们披上了仁义的假面。
等到伦敦的热度过去后,赚得盆满钵满的亚历山大把巴特曼送往不同的城市。
巴特曼抹去了名字,她被人称作“霍屯督维纳斯”。“霍屯督”是荷兰人对非洲原住民部落的蔑称,“维纳斯”是掌管生育的希腊女神,两者的结合更像是对巴特曼身体的嘲讽。
她有着人类的头脑和外表,也有着独立的思考能力,却不被人当成人来看待。
她日复一日地参展、表演,困在离当时先进的欧洲大陆,只隔了一道铁栅栏的囚笼里。很快,寻常市民就对她失去了兴趣。

1814年,她被转手卖给法国驯兽师S. Reaux,继续进行着她非人的表演。
在巴黎这片孕育了自由与热情的土地上,她和马戏团饲养的动物呆在笼子里,被要求模仿动物们可笑的神态。
她像大部分动物一样,跟着驯兽师的指令做出相符的动作。
她很少被要求表演擅长的歌舞,大多时候,只能惊慌地躲避追赶她逃跑的狮子猛兽。
但这并不能满足前来观戏的贵妇人和富家子弟,为了让巴特曼更具价值,马戏团推出了“摸臀券”。

只要花钱就可以随意触碰巴特曼的身体,甚至能用尺子测量她身上的一切。为了活下去,巴特曼沉默地忍受着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欺辱。
不过很快,她就引起了一个男人的注意。
归宿
这个男人叫做居维叶,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对人体极为感兴趣。他联系了驯兽师后,组织了多场活动,租用了巴特曼进行科学研究。

居维叶
但这场科学研究之下所隐藏的,却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歧视和“去人化”。
由于习俗和教化,巴特曼的神态动作和欧洲人不太一样,这群披着上流社会面貌的科学家将这些不同,视为“未进化完成”的符号。
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巴特曼拒绝向所有人赤身裸体,哪怕是早已被强制贴上了各种色情和低俗的标签。
未得到允许的居维叶不愿就此放弃,他向周围的人暗示巴特曼的堕落,表明自己已经有了研究非洲人的一手数据。

他以此为由,编造数据发表论文,想要证明人类进化和性器官的发育相关。在这位傲慢的科学家眼里,非洲人不过是尚未进化完全的物种,欧洲人才是高贵而智慧的种族。
这简单粗暴的结论,为欧洲扩张世界版图的野心增添了一剂强心剂,也让众多欧洲人对非洲的剥削更加心安理得。
原先还抱着一点怜悯心态看巴特曼表演的人,也换上了一副看动物的面孔。他们居高临下,而无心理负担得打量着这个身心俱备,伤痕累累的女人。
一年后,巴特曼被遗忘在马戏团的角落里,随着热度的褪去,她已经无法为马戏团再创造价值。

她被驱赶出马戏团,流亡在繁华的巴黎街道上。最终在冬日的冷风中离开了让她饱受磨难的世界,倒在了寒风中的巴黎。
周围宝马香车,华灯初上,人们裹着厚棉衣讨论着明日就会到来的新年。
巴特曼只能蜷缩在布满了湿苔的角落里,只有27岁。
这时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军队在俄罗斯败北。为了抢夺更丰厚的资源,被禁止的黑奴贸易又以走私的方式开始兴盛,烧杀抢掠的步伐蔓延到整个非洲大陆。
和她故乡的同胞一样,即使是在死后,人们也没有停止对巴特曼身体的剥削。

最先得知她死亡消息的居维叶解剖了她的身体,当刀子划过她的皮肤时,距离她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亡灵尚未安歇,魔鬼就已经伸出了罪恶的双手,他们企图再一次论证——对非洲的殖民,是在拯救人类于水火。
他们把巴特曼视为动物,用研究动物的方式和姿态,得出科伊桑人不属于人的结论。
一篇篇荒诞的论文开始发表,践踏在巴特曼身体上的笔和刀子,成为这群伪君子装饰自我的道具。

一位解剖学家甚至在记录中,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分析和猜测出巴特曼生前的景象。他认为这个死去的女人,一定是个乐观活泼,极具感染力的人。
但这还没完,因为生前轰动一时的表演,居维叶在巴黎人类博物馆中展出了巴特曼的遗体。本就不高大的巴特曼,被制作成标本分成小小的部分,零落地散在展柜里。
她的遗体成为艺术品,静静地在展馆中等着游人的到来,向他们无声地述说着曾经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一切。
20世纪70年代,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指控巴黎人类博物馆展出巴特曼的遗体。她们认为在展馆中,暴露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女人的遗体,是极为不道德的行为。

1974年,迫于压力的巴黎人类博物馆,将展台上的遗体撤下。继而又将其视为法国的藏品,收于库中。
此时的南非逐渐崛起,黑人带领的政权,逐步将自由和人权握在了自己手中。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打破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陆上种下的“种族优劣论”的魔咒,从历史和现实中探寻民族未来的出路。
他们从巴特曼为样本的研究数据入手,以更准确和更客观的数据表明,科伊桑部落的先民是非洲人的祖先。
他们和人类有着一样的身体和头颅,一样的情感和思想,巴特曼是和戏弄、围观、折辱、解剖她的人一样的人。

巴特曼不止是巴特曼,她是南非科伊桑部落的族民,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非洲人之一。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为了积累原始资本,开始贩卖和屠杀黑奴和妇女。
无情的刀刃捶打在他们身上,在武力与歧视之下,他们的人格被异化。他们被当成猪狗一样屠杀劳作,他们的鲜血流遍欧洲,成为步往资本主义曙光的台阶。
巴特曼是其中的一员,她的贩卖者延续近两百年,想要从她身上榨干最后一滴价值。
她悲惨地遭遇极具代表性,是非洲人民自15世纪以来所承受的不公,也是欧洲各国在非洲身上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的书写。

南非政府和人民要求归还巴特曼遗体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为这个生前被迫害,死后还被继续侮辱的女子而悲伤。
她的魂灵散落在外,她的苦难仍在延续。
1978年,诗人黛安·费鲁为巴特曼写下一首广为传唱的诗歌——《我来带你回家》,诗中轻轻地向巴特曼问:
“你是否还记得那苍茫草原?记得那大树下繁茂的青草?故乡天高气爽,阳光也不再灼人。”
“我来是为了把你拉开,让你远离那个人造怪物刺眼的眼睛……他把你的灵魂比作撒旦,并宣称自己是终极的上帝。”
随着诗歌悲伤又饱含悲痛的传唱,巴特曼的事迹被世人知晓。

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和学者站出来为巴特曼正名,让法国政府向南非归还巴特曼的遗体。
1994年5月11日,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上任。这位总统一上台,就致力于推进黑人的解放运动。
他深知非洲人民人格独立,在全世界的重要性。早在1992年,他就同法国交涉,要求法国归还巴特曼的遗体。
终于,在2002年巴特曼的遗体回到了孕育她的故乡盖蒙图谷。漂泊近200年的灵魂安息于故土,8月9日南非妇女节这一天,她从“物品”回归了“人”。

南非人民为交涉的成功喝彩,也为巴特曼的回家痛哭流涕,巴特曼成为南非的民族英雄。
她没有带领过人民反抗,也没有成功反抗过任何一个人。她无比弱小,最后成为了一个民族反抗的符号。
在漫长的非洲被剥削史中,所有的非洲人都是不独立的人。他们被帝国主义的强权压倒了头颅,被当作牲口侮辱,被当时的主流排斥在人类之外。并以此为借口,对非洲展开名正言顺的殖民。
在巴特曼被归还的那一刻起,以她为样本对非洲人民“非人”的叙述和论证都已荡然无存,非洲人民打破了身上的锁链。

如今,巴特曼戏剧化的一生还在被不断质疑和解读。
有人正在遗忘,模仿着以她为原型的现代画拍摄杂志封面,也有人将她的墓碑上喷染了厚厚的白漆。
作为非洲黑奴和妇女被贩卖历史的缩写,巴特曼永远警醒着世人:
科学和发展的底线是人权与自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违背了人类发展的最终指向和目的。人之所以为人,需要不断反思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愿巴特曼魂灵永安,愿世界不再重蹈覆辙,愿人类自由和平。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66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