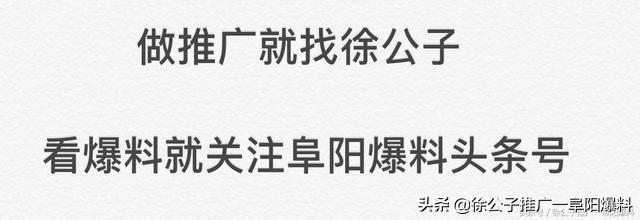「供销社印象7」 缝纫社
从川西高原蜿蜒而下的徐堰河奔流到新民乡地界,变得既平顺又温柔。即使拦腰穿过新民老街,在我看来,那不是鲁莽,而是暗含期许的勇蛮。一条古河与一条老街的相遇,多少柔情缱绻,多少离愁别绪,是你坚强了我,还是我软化了你?徐堰河流淌着。老街沉默着。时光在徐堰河的旋涡里打转,历史在老街屋瓦的青苔上沉淀。
河上的清安大桥始建于清初,后几经冲毁,又几经重建。我上小学前,桥还是搭在水面上的木板浮桥,一截一截地相连着,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甚是可怕。洪水季节,浪涛汹涌,木桥在水中时隐时显,根本没人敢过河。桥头两岸挤满挑担、推车、提篮、背娃的赶路人,焦急地等着水退。
70年代初期,全公社人民战天斗地,新建了在当时堪称雄伟的清安大桥。自此一桥飞架,两岸贯连,老街换新颜。
公社缝纫社在清安桥头(南),我大孃家在清安桥尾(北)。徐堰河昼夜流淌,涛声不绝于耳。

缝纫社铺面有两进。第一进为前堂,窗户向街沿推开着,窗台下横陈一张光滑的乌黑木质工作台。老而瘦的顾裁缝,跛脚,吊着细细绳的花镜垮到鼻梁,肩上搭着长长的软布尺,手上青筋暴露,手指像鸡爪,身子像是俯在桌台上,呼,呼地在布上画粉线。
第二进为缝纫间,与外间一样宽,却长很多。内里有8台缝纫机,两台为一组,分别靠近两边墙壁并排摆着,中间留一条宽宽的通道;前后共摆四排,很是整齐。
我大孃是缝纫组的组长,坐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我未来的表嫂坐在她的身后,我未来的小舅妈坐在最后一排的左边。
我翻过门槛去缝纫间找我大孃,仿佛走进织女穿梭的瑶台仙苑。8位仙女脚踩踏板,手移衣料……缝纫机莺莺燕燕,软布料顺顺滑滑,有动听的声,有轻巧的形。这样的场景落在心上,便是我潜意识里最原始的美学启蒙吧?劳动之美,与音乐、舞蹈、思绪相关联。
供销社布匹店就在缝纫社隔壁。当年买布,不仅要有钱,还要有布票。逢年过节买一回,还大多用于走亲戚送礼。但手里再紧巴,总有给自己做衣服的时候。
一家人相跟着来到布匹店,看好货色付了钱和票,捧着布料抬脚来到缝纫社。我大孃面无表情,高傲地接待这些内心卑微而又激动的乡民。顾裁缝根据我大孃的吩咐立马量身高、量腰围;织女中哪位手中活计短,我大孃就安排哪位接新活。一件新衣服,大致三五天就可了。
小时候母亲带我到缝纫社做新衣,这铁定是有的。但我现在委实记不起做过什么衣服,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只记得我未来的表嫂从顾裁缝手里拿过布尺,亲自给我量尺寸。她的手触到我的肩,有一种清凉的气息。

我大孃最终还是在1950年由宋家湾嫁到场街老杨家,当上了堂堂正正的城镇居民。在我印象里,大孃从不笑,一直是权威而凛然的。不仅老杨家和宋家,连缝纫社的大凡小事,都得由她做主。
大表姐在遥远的阿坝州大山里当知青,小表哥在街上做杂工。我此生第一次吃到苹果,就是大表姐从阿坝州带回来的。现在还能记起她坐在我家茅屋房檐下,一边削苹果一边同她小孃(我母亲)摆龙门阵。檐外雨水滴答。当时我母亲抱着我二妹喂奶,据此推断,我应该在三岁上下。
小表哥憨厚,朴实,脸上常年挂笑,他没有读多少的书,经常被我大孃骂,却很是恭顺。我去大孃家玩,看见大孃就生怯。唯有单独与小表哥在一起时,开心得不得了。
解放以后,我小舅已别姓他家,但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他虽然跟着别家(养父),但早就把宋家湾和我大孃家当做自己真正的家。这两处都专门给他留了房间。
我晓事时,小舅已是新民乡很有名气的读书人。他因身世坎坷,读书和劳动都很用功。他高中毕业遇到取消高考,只好回乡劳动。在公社建筑队的搬砖工人里,他是属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里,他是属于吃苦耐劳的搬砖工人。总之,他身上散发着很接地气的文人气息。这或许也是他后来能担任领导,并在离职后还能在房地产做成一番事业的密码吧。
我之所以要简略地介绍与我大孃相关的亲人,其实是想讲一个复杂的家族故事(详见后续宋家湾往事),他们都因为我大孃的强势而改变了各自命运。
比如那位在缝纫社坐我大孃身后的“我未来的表嫂”,其实当时是我小舅的女朋友。我小舅从建筑队下班,路上看到缝纫社还亮着灯,便大姐大姐地招呼着我大孃,然后走进缝纫社找他大姐。他与这位织女的缘分应该也是顺理成章,她本可以做我小舅妈的。
那位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未来的小舅妈”,本可以与这个家族不发生关系的。
但我大孃却为我小舅、我小表哥、我未来表嫂,我未来小舅妈写了一个我不敢评价的故事。
我大孃上月过世,享年89岁。在她生前,我无数次想向她探询“我表嫂”“我小舅妈”的故事详情,因怕挨骂,终是不敢。
我小舅于2018去世,我小表哥更早在二十年多前就英年早逝。我小表哥去世后,我表嫂果如我大孃所愿,独身守候照顾她二十多年。

缝纫社自成立起,我大孃就一直担任负责人,直干到退休。退休后,这个位置才由我表嫂接替。
大约是1985年夏天,我中师毕业后在邻乡一所寺庙改造的村小学教书。其时,农村大地忽然刮起“西服旋风”,凡有钱、有势、有地位、有面子的人,都纷纷穿上西服,成为当时一景。
我虽然还不到20岁,但我妈“担心你娃找不到婆娘”,除了把我工资没收之外,还添了点钱,执意要为我做一身抬高身价的时髦行头。
布料是在县城选的。选好后,我妈带着我去大孃缝纫社。
那时,缝纫社还在,顾裁缝已逝,早前红火的景象已经不在。
整个缝纫社,居然没有人知道西服怎么做。
隔壁大队有一个年近70岁的老裁缝黄裁缝,曾因本人出身问题和祖传手艺遭到批斗,几十年默不作声。恰在此时,他像雨后青草一样冒了出来,精气神十足。四乡八邻的人纷纷前来找他打西服,最长时间排队到一个月以外。
于是,我今生的第一套西服,便由这位旧时代过来的老裁缝亲手制作。
我大孃、表嫂所在的缝纫社,自此渐渐地走了下坡路。
后来,我穿上这套西服,周吴郑王去追女朋友,却并不顺利。那些典雅又高深的姑娘,怎么可能看不透伪装之下的寒酸?
而我也终于知道,任何富丽的包装,都无助于抬高自己的身价。
当我明白这一点时,爱情也不请自来。

(图片来自头网络,若有侵权立删)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759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