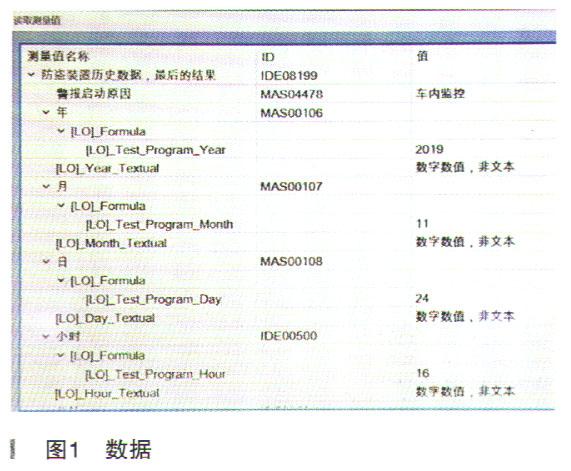童年记忆里的喇叭头
童年记忆里的喇叭头
文/范博文
我在童年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村西头的西坡上。
爷爷奶奶的院子有三间北屋,是父亲费了好大的周折,分两次才勉强盖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三间房子,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房子建好了以后,父亲便把爷爷奶奶安置到了这里,爷爷奶奶带着我住了进去。

住进去不久,就赶上公社里来人给社员们安装小喇叭,我们叫喇叭头。说是装上了喇叭头就能听到大山外面的声音了,还有天气预报,还能听歌,听相声,啥都能听到,真是太好了,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啥是相声。喇叭头家家户户都有份,头回见那喇叭头,黑黑的,外面方形,里面是圆的,中间凹进去,看着就是个浅浅的碗,摸着就是黑黑的纸做的,但是后面却是有点重的,后来我知道,里面有一块吸铁石。
一条细细的电线,从东家串到西家,把每家每户都连起来了。爷爷让装喇叭头的人给我们安在卧房里前墙窗户的上方,一条细细的铁丝从窗缝里穿进来,接在喇叭头上,又从喇叭头接出另一根线,再从窗缝穿出去,连上一块小铁棒,把那小铁棒埋到墙根的土里去,在上面浇上一瓢水,如果是浇上一瓢浓浓的盐水就更好了。当时我啥都不懂,后来知道,埋入地下的那根小铁棒是地线,没有地线,喇叭头就不响了。至于那喇叭头就用一条绳子栓住,用一个钉子歪歪扭扭挂在墙上了。
那装喇叭头的师傅倒是挺麻利,不一会儿就装好了。
我问他:“你怎么不让它响啊?”
他说:“现在还不响,等过几天,都安装完了,家家户户的喇叭一起响。”
我问:“怎么个响法?动静大不?”
他说:“不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都是能听到什么呀?”
“放啥听啥,啥都有。”

然后他就那样走了,去下家装去了。我就在想,到底能放啥啊?又憧憬又纳闷,这里面能有啥?当然,我是不会认为里面有小人的,因为我知道是科学的事情,只是不明白啥道理罢了。
就那样过了很多天,也不见那装喇叭头的人了,我心里在嘀咕,是不是都装完了?不是说装完了,就响吗?怎么还不响?
放学回到家,我会竖起耳朵静静地听听喇叭头是不是有动静,还会爬到炕上去,把耳朵贴在喇叭头上听,啥都没有,心里便有些失落。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还在睡梦里,一种声音把我吵醒了,朦朦胧胧听到《东方红》乐曲声,立刻辨别出是头顶上的喇叭头响了,声音很清晰,《东方红》乐曲即熟悉又亲切,是我上学第一天唱的歌。
听到了响声,心里很激动,我便开始咋呼:“爷爷,爷爷。”
咋没有爷爷的声音,屋里没人,我顾不得穿衣服起床推开门,看到爷爷正在扫院子。
“爷爷,爷爷,快,快,快来啊。”
“看你急急呼呼的,咋了?”
“响了,响了,喇叭头响了”
爷爷放下扫帚,来到屋里。
爷爷说:“真的开始响了,真好,以后就能听广播了。”

没多大会儿,就听喇叭头里开始嘀——嘀——响了几声,然后说:“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七点整。”
“听到没,爷爷,七点了。”
爷爷下意识地去看挂在里间墙上的那个挂钟,自言自语地说到:“怎么差得这么多。”
我抬头看看那挂钟才五点多。
说起爷爷的挂钟,奶奶有说不完的抱怨。爷爷为了上班有个点,便从委托部花了三块钱买了这个二手的老挂钟,从买回来就没正点走过,倒是请人修理的次数不少。

您会疑问,爷爷不是农民吗,怎么会上班?
爷爷不是农民,是工人,父亲也是工人,我们的家庭,是有工人的农民家庭,这是个故事。
一个本家的邻居,按辈分我叫他六哥,虽然他辈分小点,但是年纪比我父亲还要大。六哥会些修理小物件的本领,爷爷的挂钟从抱回家来,就没少让他来修理,感觉那个时候,我看他修理挂钟都上瘾了,感觉好有趣味。只是我不懂,就是看着他拆开了,一个个齿轮取下来,开始清洗,然后再装上,再上一点油,每次都是那样,可还是跑不准。而他每次见到爷爷,都会问及钟的事情,爷爷便说,你上次修过后,跑得挺准了。
奶奶却颇有微词,说人家不要了的东西,爷爷还当个宝买回来,能有好吗?
有了喇叭头以后,爷爷便再没有修理那挂钟。
打那以后,我觉得生活丰富多彩了。每天听广播和现在看电视一样,了解了国家大事,还能听文艺节目,只是每天分时段播放三次。
早晨六点多钟,《东方红》乐曲开始响起,然后传来播音员清脆的声音:“乐疃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接下来便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然后继续播送一些新闻,文艺节目,最后是天气预报。早上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播送时间。中午和晚上也有,晚上的播送时间会长些,一天的节目就在《国际歌》乐曲中结束了。

那时,喇叭头每天都在播送“政治挂帅、纲举目张”的内容,天天都有“最高指示”播出,生产队都要求社员收听、学习。能经常听到农业学大寨的事情,说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故事,只是那个时候我始终没弄明白狼窝掌是个什么东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月,喇叭头是让我认识大山外面的世界最有帮助的东西了。
《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都是我最喜欢听的。有时候会播送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段,爷爷会跟着哼几句,我却一点不懂。
就这样,喇叭头伴随我快乐地度过了好多年。
有一天,喇叭头不响了,因为我从安装喇叭头的人那里知道,浇一瓢水到地线上,就会响,我便学着,浇了一瓢水,仍然不响,过了会儿,又浇水,还是不响。唉,我是无能为力了。
隔着我家不远的邻居,是队里的电工,那个时候觉得电工太厉害了,让我崇拜得不得了。队里的电他都管着,还管着电磨房,晚上,只要他不送电,全队的人都摸黑。

他有权利给家家户户的电灯上贴封条。
贴封条就是用一块纸抹上浆糊把灯泡和灯口贴住,让它俩牢牢地连在一起,为的是怕有人偷偷地把灯泡换大了,那样就是在偷电了。因为每家每户都是按照统一的数额来缴电钱的,所以必须用一样大的灯泡。不过,各家可以按照自家的需求用灯泡,有的用二十五瓦的,有的用十五瓦的,当然,瓦数不一样,电费也是不一样的。就怕有人佯装十五瓦的,晚上偷偷换上大的,那样队里的电就亏了。所以,必须把电灯口贴住,贴住了,就不能动了,如果动了,那层纸是必然会开裂的,电工就知道了。
有一天,队里电工路过我家门口,爷爷便询问他喇叭头的事情,他进了我家,三敲打两敲打地喇叭头就响了。太无语了,早知道,我也敲打敲打不就完了?
不过后来,我是真的没少敲打它。喇叭头就挂在窗户上方,每天烟熏火燎的,日久天长上面存了厚厚一层灰,有时候一敲,会有许多的尘土落进嘴里去。

后来的某一天,我忽然听到东南面的莲花山有广播的声音,那声音好大,又大又清晰。原来,生产队里在山上装了大喇叭,远远望去,一条水泥杆上装了三只大喇叭,朝着村子的各个方向。打那以后,大喇叭就彻底盖过了喇叭头了。
生产队还可以用大喇叭广播各种通知和队里事情。真是大喇叭一响,全村回荡。
……
多少年过去了,童年那伴着喇叭头成长的经历总是绕不开。虽然回荡在家乡的声音,早已成为过去,我却有无数次在梦中回到那难忘的岁月,那扎根于心底的歌声怎么也忘之不去……

仿佛那嘹亮《东方红》乐曲始终在耳边回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 ,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得————解—————放—————”
壹点号 独有至贵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1500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