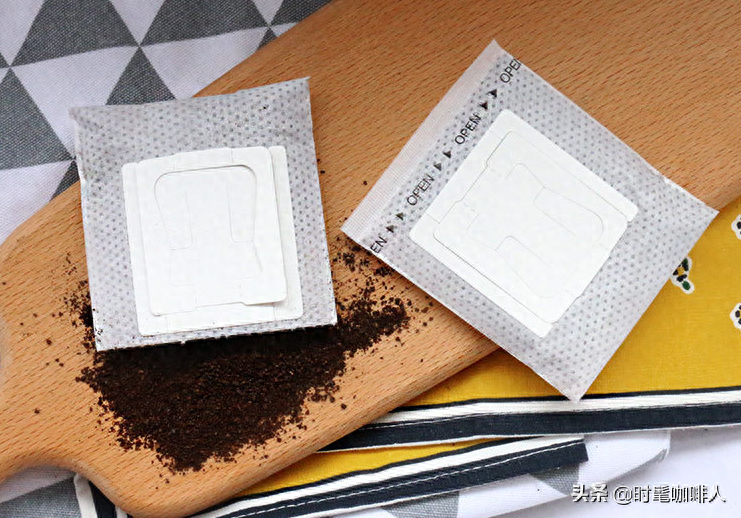罗朗在马背上的 13 个时刻

罗朗(Michael D. Rosenblum)的人比他的菜有名。食客、厨师同行、饮食学者、纪录片导演甚至他的文化经纪人,都是先知晓这人,再来尝他的菜。了解真正的罗朗是困难的,他太杂糅 —— 作为一个文人和厨师,一个名人和普通老百姓,一个局中的外人和永远的第三方观察者,一位有抱负的人类学者以及饱受偏见的美国犹太人 —— 一如他在采访中提及的伟大作家、人类学家,总是一言难尽,也拒绝被轻浮的概念勾勒。
但罗朗的菜里埋着一条暗线,这条暗线就是他的观察、感受、记忆、情感,那些不动声色的幽默、无法安放的愁绪以及一种悲悯万物的佛家世界观。可以这么说,罗朗的菜就是他的传、他的道、他的佛经以及他诸多「在马上」的时刻。

惊蛰当天,忙活了两整日的罗朗终于得空坐下。话没说上两句,他叫停了编辑倒茶的手 —— 茶汤颜色不对。白瓷盖碗停在半空,他接了过去,半分钟,茶叶被水浸润,一滴、两滴,茶汤滴落的速度与脉搏同步时,变为色泽更为深邃的茶汤。「茶人常说,做茶是半个师傅,泡茶是另外半个。很贵的茶,泡不好,也是一堆废水。」他的声音散淡、和缓,像清水一点点往外漫。
昨夜 20 人的晚宴让团队人仰马翻。他走路也恍惚,却依旧摇头,「只做到了脑海中的三成。」「一咏三叹」里,用来点缀炸乳扇的臭草用的不是最嫩的叶子;「牧民餐桌」里,藏包的孔洞数量不对;「水城烤洋芋」的摆盘太过单一,没能复刻出记忆里的灵动模样;「穗蟹卷」本想做成帝王蟹的花纹,最后只做成了花蟹的纹路。「少城意境」更是深深的遗憾:时间太紧 —— 做银杏叶的模具昨天中午刚到;人手不够 —— 他临时叫回了曾经的徒弟陈涛,团队还有待磨合;还有运营成本考量 —— 他不得不在举办活动的同时接待付费客人。


水城烤洋芋。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2021 年 10 月底,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农业贸易处找到罗朗,计划在朗泮轩办一场晚宴,邀请广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三地的各大名厨出席。因为新冠疫情,晚宴时间一延再延,最终定在了惊蛰前夕。3 月的广州是名副其实的花城,木棉、紫荆、杜鹃、三角梅,一路姹紫嫣红,空气里都是春的信物。
食客之一的陆小姐在朗泮轩天台闻到一阵奇香。她问正在处理植物的罗朗,这是什么树的味道。罗朗回答,这个不是树的味道,也不是不是树的味道,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春天是什么味道呢?没人说得清,但当它到来时,每个人都闻得到。这便是艺术生发的空间,唯有它能追溯经验中的微妙之处。
罗朗念念不忘的春天味道在十多年前的成都街头。雨水和惊蛰交替之际,春雨降临,桃李次第开放,上个秋天落下的银杏叶还留在街头茶馆废弃的茶碗里,荡起涟漪。当晚,他以川菜鸡豆花作「水面」,宋代汤饼作「银杏叶」,呈上了这道「少城意境」。「那些我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小商店,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我的记忆还在,它被捕捉进这道菜里,带着我对春天的憧憬和希望。」罗朗在菜式卡片上这样写道。

少城意境。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今年 2 月,罗朗去成都参加活动,带回来几片近乎完美的银杏落叶。他找到模具师傅,照此制作了套银杏叶的模具。原本设想里,这道「少城意境」将会是一座看不见的桥梁 —— 连接着雨水和惊蛰,过去与现在,东方和西方。
桥梁并未被成功架起。银杏叶的颜色不够自然,罗朗脑海中的颜色是绿中透着一点点黄,似真而非真。在那之下,还藏着一层他关于时间的哲思,「世间万物转瞬即逝,这个春天过去了,就再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做的菜,下一个春天再做,也都不一样了。」

晚上 7 点,天暗下来,房间里烛光摇曳,如蝴蝶振翅般扑腾着的火苗一一抚过有竹节的筷、玉兰花式样的筷架、海底沉船的瓷器碎片。一张盖有「雨水」闲章的菜单递上,菜单上 12 道菜式如下:
一咏三叹 Three Seasonal Refrains
穗蟹卷 Crab Shell Pasta
琼州凤谷 Hainan Chicken Rice
水城烤洋芋 The Potato Vendor
少城意境 Chengdu Tang Bing
江湖海扇蛤 Scallops in Chili Broth
猪肉颂 Su Dongpo's Ode to Pork
奶汤霜禄汇 Mallows in Milk Stock
牧民餐桌 The Herdsman's Table
竹叶青 Spring Bamboo
寺洼鬲粟 Culture
果脯 Something Sweet
其中七成都是第一次做。罗朗为每一道菜写有一段文字,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不等,印在一张张白色卡片上,上菜前,同刀叉一同置于食客面前。卡片上的讯息不比菜式少 —— 从丝绸之路到寺洼文化(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从《齐民要术》到《随园食单》,从七八千年前的古老谷物到唐代以前的蔬菜上品,每一道菜的灵感、做法、器物以及背后的故事与思考,事无巨细地呈现。

在朗泮轩的春季菜单上,盖上了「雨水」闲章与中文名「罗朗」、英文缩写名「MDR」的名章,并签上了名字。
罗朗将它们也视作菜式的一部分。在他的菜里,重要的不仅是菜式本身,还有它们如何讲述自己。「一顿饭唤起的觉知不亚于看完一本书。」食客之一的鲁西西感慨道。美食专栏作家林卫辉也说,每次在朗泮轩吃完饭,回去都会不自觉拿上几本书翻一翻。
这餐的新知是葵菜 —— 一种已经从餐桌上消失的绿叶菜,口感类似莼。罗朗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得知了它,其中《种葵》被列为蔬类第一篇。在明清以前,它是普遍且重要的蔬菜,白居易曾写诗道「绿英滑且肥」,令罗朗神往已久。种子并不好找,副厨闫祺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罗朗称,传家宝般的种子。
「所有菜里,这个是最简单的。」耗时却最长。葵菜种子在去年 10 月种下,从播种到上桌,全由罗朗和员工一手打理。奶汤也吊足一个礼拜 —— 选择胶原蛋白最丰富的猪膝关节骨,一遍一遍用温水浸泡,直至再无血水,再和自制风肉、鳕鱼一起熬制,如此出来的汤纯白、温润,有羊脂玉一般的光泽。

奶汤霜禄汇。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泰安门副厨林裕立是当晚受邀主厨之一,这是他第二次来朗泮轩。去年秋季菜单上一道「葱烧酱鸭」至今印象深刻 ——「很少人会想到用荔枝来配鸭胸」。起初,他笃定罗朗做的是西式料理,依据是厨房里齐全的西式烹饪工具以及菜式的料理技法,但细想过一番菜式后,他又收回了这个判断。「他所用的食材、呈现方式和讲的故事又不是西方的,我觉得我定义不了。」
罗朗的视角里,自己毫无疑问做的是中餐。但到了现在,他觉得中西餐的讨论已无甚意义。「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中餐是什么,西餐又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人造的概念,就像贵价食材和平价食材一样。」
局内的外人,中国文化的第三方观察者,一个一直「站在中间」的人,罗朗这样定义自己。纪录片《厨房里有哲学家》里,他把自己比作二胡的弓,中国和美国,两边都不站。「(二胡)弦跟弦中间是什么?空。但只有在空的地方,才有机会拉出漂亮的音乐。」
音乐家通过音乐了解世界和探索自我,作家通过文字,罗朗则是 —— 开一家餐厅。

朗泮轩至今不曾盈利。作为餐厅「大脑」的主厨罗朗,从开业到现在,只有其中两个月给自己支付了半个月的工资。必要时,还往里贴钱。
2020 年 1 月,朗泮轩刚开业,便赶上疫情。再开门,已是盛夏 6 月,半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两年里,类似情形一次次重演,眼见生意刚有起色,一个浪头打来,又被荡出去好远。「现在基本就是保本的样子。」罗朗说。
餐厅开在广州沙面北街,往南隔着一条人行道便是珠江,往北是清平中药材市场和曾经闻名天下的广州十三行(清朝对外贸易机构)。以珠江为界,河南、河北是本地人的称呼,朗泮轩在河北,林裕立在对岸的河南长大。他熟稔这个城市的一举一动,尤其餐饮业,「一些人开餐厅是做生意,罗朗可能只是想开一家自己的餐厅。」他诚实地说,「我不太能看到这个地方的 promotion(推广)。」
文化人而非生意人,是诸多餐饮从业者对罗朗的共通印象。林卫辉说,罗朗只要在广州一般都在厨房,如果想约他到别的地方,他都不太去。

在广州的罗朗,大多数时候都在厨房。他小心地用镊子将采自楼顶菜园的花草置于菜品「水城烤洋芋」顶端。
他有意躲避这个圈子。在主厨光环日益盛行的当下,他过着一种俭朴的生活,与植物、土壤、平头老百姓交朋友,对高端餐饮的自视甚高不感兴趣。在一些过于正襟危坐的宴席场合,他心里想的是,幸亏我不用坐在桌子上。
各大餐饮奖项也不曾光顾过朗泮轩。有趣的是,罗朗本人倒曾接到过几次米其林和黑珍珠的活动邀约。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被误解和被低估的。一个外国人做中餐,怎么可能会好吃?他的第一本书《美食之路》(FOODWAYS)写的是美国饮食文化,那是妥协的结果。事实上,罗朗最初想写的是一本关于中国各地传统手工小吃的书。那段时间,他几乎跑遍了各大出版社,他们总是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写你比较懂的、自己的东西呢?罗朗回答,我几乎就是在中国长大,在美国也是跟中国人在一起,从十二三岁起吃的就是中餐,童年的味道就是茶、肠粉、煲仔饭以及各种炒菜。但那并没有改变什么。
人活在自己观念的围城里,傲慢与偏见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兀自生长。「难道就因为我出生在美国,就比住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研究美国文化的中国人更懂美国吗?」罗朗觉得荒谬。「你比我还懂中国菜」的言论,他听人说起无数次,夸赞之下,并不难嗅见其暗含的一丝偏见意味。「如果我开第二家餐厅,换一个名字做同样的东西,但从来不出厨房,对外就说是某位罗师傅做的,我相信一定会非常受欢迎。」他不苟言笑的脸更添了一份愤懑,像一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

在为视觉带来享受之余,这些可食用的花瓣、春草也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或酸或甘,偶尔带有苦与辣。
外国人的身份之外,罗朗认为,更大的障碍如高克宁所说,你出生在了不对的时代。「我可以感觉到我跟现在的人是无关的,或者肯定是有一些障碍和距离的。」最显性的,对于一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践行。他坚持手工古法酿制的酱油 —— 大豆经自然光晒和瓦缸发酵,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自己发酵醋,制作虾酱、腊肉。楼顶天台种有薄荷、罗勒、辣椒、柠檬等数十种蔬果,从播种、施肥到收获,全部亲手打理。器物更甚 —— 平常「虐」惯了周围人的罗朗,在景德镇的手艺人那里也尝到了被「虐」的滋味,为了一只罗汉竹的漆器,他苦等两年多,就「死」等那一人。
风味上的微妙差异,有多少能抵达食客,罗朗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问问你自己,你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人类学家克洛德 · 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曾在著作中带着愤怒写道:「人类陷入了单一文化,准备生产大批量的文明,如种甜菜一样,以后大家的日常伙食就只有这盆菜可以吃的了。」罗朗也有相同的感受,「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单一,原来我们有 3 万多个品种的苹果,现在作为经济作物进行大规模种植且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可能就只剩下不到 30~50 种。但很少人关心这个。」他想得更多,也更远。「当你亲自参与过一棵菜的浇水、施肥,哪怕一片叶子掉落,都会特别珍惜。但如果就是在超市随便买上一包,跑腿送过来 1 个小时,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循环会越来越有距离感。」

采自楼顶的油菜花。

来自楼顶的桂花。
另一个问题更发人深省:你想如何度过你自己的时间?诚实说来,时间并非对每个人均质存在,你站在什么维度看时间,时间也会相应地装扮你。对于一位每天在厨房工作十来个小时的厨师来说,是机械式地重复利用鹅肝、鱼子酱,让时间在毫无意义中流逝,还是一点一滴地浇灌、把时间倾注在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上?答案不言自明。当我们问他为何要坚持手工时,他说,「我并不是为了你们,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他指了指背后的房间,「我是为了他们(朗泮轩的员工)。手工的真正价值在于做的过程,而非目的。」它抵达手头的食材,也愉悦制作者的大脑。
记忆里有好些个夜晚,罗朗和员工们在厨房里做「黄瓜沙拉」:天台菜园里种的茉莉花、薄荷加上切得极细的黄瓜条,手工编织成一只只玲珑小球,每只耗时两小时,偶尔忙到凌晨,他们就会放佛经来听。那时,厨房就变成了庙宇,在一种沉默、收敛而又安详的关于自我意识的进出中,人进入一种近乎禅想的状态,内心充盈而满足。「这就是过程的价值,就是『在马上』。」

罗朗在广东汕尾市红海湾遇到了他的新朋友白马「大白」,骑马是他在厨房之外另一个获得自由与平静的方式。

罗朗童年时期骑马的照片,同样是一匹白马。
1979 年,罗朗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第二大城市圣安东尼奥,那里是著名的牛仔之乡。9 岁那年,他学会了骑马。「从小我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孩,骑马让我放松,就像我偶尔给朋友和家人做饭。」在一次次切煮、搅拌、进出烤箱的动作中,意识被放逐到很远的地方,人觉得放松而平静。他给我们看一张他少时骑在马背上的照片。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绵延的群峰下,他穿一件格子衬衫,跨坐在一匹白马背上,转头看向镜头。那会儿他便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但微微笑着,看上去比现在快乐。

在更深入了解罗朗是位什么样的主厨前,不妨先来听听他是一位怎样的食客。
跟随他 12 年的副厨闫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家所谓高端餐饮的餐厅,茶壶里的水空了半天,服务员走来走去,都当没看见。罗朗左手撑着脸,右手悄没声息地靠近空茶杯,一点点地往餐桌边缘移动,「啪」,杯子应声落了地。瞬间,5 位服务人员围了上来。同样是那顿饭,后半程想加菜,还是半天没人搭理。这回遭殃的是一只空餐盘,依旧「在沉默中爆发」。
有时他们去一些大众餐馆。罗朗问老板,有没有尖椒肉丝,老板答,我有尖椒也有肉但没有尖椒肉丝。罗朗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进厨房自己炒一个。在贵州山区采风,闫祺口中「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找到一家能做炒菜的小馆已属不易,罗朗看到已经切好、调味的肉,转身问老板,你这肉有没切的吗 —— 他想要刚切出来新鲜的肉。
员工们后来学乖了,和老板一起出去吃饭这事,能免则免。但老板在厨房里的要求,还是要尽全力满足。闫祺见识过他发大火的样子。2011 年,在成都岷山饭店,当时这个四川姑娘还不是厨师,汶川地震后,她从导游转行做酒店前台,做了 3 年,正处职业迷茫期。一天,她听说楼上西餐厅刚来的外国主厨拿来一只垃圾桶,把厨房里所有没达到他要求的成品、半成品,「唰」一下全扫了进去,然后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他『优秀』的脾气。」闫祺说,「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身边的人也各有各的个性,一直跟着他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诉求。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人讨厌归讨厌,但他确实有本事让我服。」
老板总有让她意想不到的新创意。「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就跟历险一样,不会无聊。」为了「穗蟹卷」的花纹,有段时间,闫祺和另外三位厨师在厨房试验到凌晨 1 点,也不觉得累,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更自然。员工常打趣老板,每次新菜单上至少有一个「变态菜」。他们一边抱怨,一边甘之如饴,知道那是技艺精进的必经之路。

「穗蟹卷」是带有蟹壳花纹的肠粉。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真正让闫祺「忍无可忍」的是电磁炉上的一只开关。每天清洁阿姨下班前,都会把它取下,用水冲洗后再安上去,「跟新的一模一样」。老板还是不满意。那天,罗朗示范了一下何为真正的干净 —— 取下开关,用牙签、镊子将缝隙里的残渣一点点挑出来,再清洗、安上。
「那个不是对客的,老板。是我们!」闫祺声音高了几度。
「对自己的,那更重要。」老板依旧一板一眼。
「但那个地方,我平时按下去后,根本都看不到。」闫祺继续争辩。
「所以这就是敏感度和感受力的训练。」罗朗顿了顿,叹口气道,「但同样的问题是,你很容易得强迫症。」

这是一个一眼便能瞧出强迫症气息的厨房。墙上的木架,陈列着不同长短、粗细、材质的擀面杖,不同用途的刀具也以同样方式归置妥当,杯、碗、碟按色泽、大小、质地分置于不同玻璃柜里。洁净、精准、缜密,和它主人常年梳得一丝不苟的偏分金发一样。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作家若泽 · 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写给世人的箴言,也同样适用于一位用五感与世界交流的厨师。罗朗自认为用心良苦。
「我让他们这样打扫卫生,他们觉得没道理,但如果你坚持细节的训练,到时候你走路,就能看到光线的影子,如果你烧香,也会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个菜。」他说着话,视线却越过我们,望着午后墙面上的斑驳光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光线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位移。你毫不怀疑,当真问起,他能准确道出某个当刻阳光的大小、方位甚至颜色。

3 月上旬,樱花在晚宴一周后绽放于空间一角。中式家具、门神画片都为罗朗的收藏。
灵与肉,身与心,精神与身体的相辅相成,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讨论,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都多有涉猎。20 世纪中后期,认知语言学家乔治 · 莱考夫(George P. Lakoff)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embodiment(体塑)」理论,用来强调「身体」在「塑形精神」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罗朗最近正在研究其派生出的 embodied knowledge(体塑知识),认为知识住在人的眼睛、耳朵、手上,而非脑海里。在中国西北,他曾跟着当地人学习用「老肥」发面,不用任何科学度量工具,用手拍一拍,听声音,就知道那个面有没有醒发好。
烹饪的极致,在于看得见的味道和听得出的颜色,厨师除了反复磨练感知,别无他法。「张祎就是把这个理念吃进去、消化,并且变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那是一位不久前离开朗泮轩的厨师,刚夺得 2022 年圣培露世界青年厨师大赛中国大陆赛区冠军。离开的理由并不难推测,但罗朗两次提起她时,淡淡的语气里都是赞许,「本来也不是要在这儿待一辈子,技术足够稳定了,就可以自己出去,走下一步,对吗?」
处理和团队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长久以来,罗朗都希望建立一支团队,彼此像家人一样工作和相处。美剧《熊家餐馆》(The Bear)里,主厨站在身后大吼 「你什么都不是」的场景,他自己经历就够了,并不想带进厨房。但他又无奈地发现,像家人一样的团队并不现实。「这是一个悖论。你要让他们(团队)舒服,你就会很难受。」
偶尔,他会故意当一个坏人,让所有人讨厌。他说,这样他们会比较团结,但我会非常孤独,只能找心理医生。还有狗。但狗又不是人。

如果此时高克宁在场,她一定会在桌下狠狠踹一脚罗朗。作为他的经纪人,她多次提醒过罗朗,看心理医生的事不要对外说,不了解的人会因此心生偏见。但罗朗坚称,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厨师、作家、品牌大使的职业身份下,也是一个普通人,有普通人的问题、普通人的困惑。他始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一个一直在焦虑地抠指甲的普通人。」
他的骄傲只在于自己做的东西 —— 所有菜式都是有感而发。「我有感觉才想做这道菜,给人分享我的美好经历,偶尔问一句,你有意识到吗?你有体验过吗?你也会怀念小时候那些美好吗?现在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还是有更好的方式?」
好的艺术让人感同身受,它们提问,而不是说教或模仿。每做一道菜之前,罗朗都会问自己,你自己的部分在哪里?「Honesty(诚实),是创作的基本。」他沉声道。人类学的第一堂课,教授没有讲任何理论,强调了很多遍「Academic honesty(学术诚实)是第一」,如果用了别人的文字,就必须标注引用。他和教授开玩笑,如果餐饮这一行像做学术这么严谨,大部分餐厅都要倒闭。
食物对他来说便是无比诚实的事。加入蜂蜜,就会变得甘甜;加入香草,就会有香草的味道;面团如果醒发不理想,就会干瘪变形;烤箱温度不准,就不可能得到一块可口的糖火烧 —— 每一步都有回应。

「一咏三叹」由三道前菜构成。图片为第三道乳扇。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高克宁告诉我们,她和罗朗的信任是从带他上了谈话类节目《圆桌派》后建立的。在此之前,罗朗被人「坑」过很多次。有人找他拍纪录片,把他带到西北,拍到一半说资金链断了,再无下文。
起初,朗泮轩为罗朗和高克宁一同创办,为筹措资金,高克宁找来了四位股东。疫情、时局以及彼此价值观的差异,合作并不愉快,2021 年,所有人退出,餐厅法人变更为罗朗自己。「他绝对不是一个让合作伙伴舒服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也是我们现在还能继续合作的原因。」高克宁说。股东退出前,餐厅过了一次账目,罗朗连买一块抹布的钱都记录在册。其中一位股东自己也开餐厅,感慨道,像这样细的账,自己都做不到。
除了诚实,还有不避讳,罗朗不避讳谈论自己的痛苦。2018 年至今,他看了 5 年心理医生。少时不愉快的经历如烙痕般刻在心上,挥之不去。有时他坐在那儿,会感觉心跳突然加快,身体开始出汗、发抖,恐慌席卷全身,以为死亡即将降临。
心理医生不提供解决方案,他们倾听,然后提问,就像他料理食物一样。罗朗觉得过程也有点像打坐,或是在马上,目的不是放松,而是让思绪慢下来。「恐慌或焦虑时,就像堵车的高速公路,我们站在马路中央,前后左右都是车,无法动弹,那个时候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稍微退后一步,退到马路边上去,你看着这个车过去,然后那个车过去,慢慢不堵了,路也就通了。」

「在马上」成为罗朗精神世界的一种隐喻,它与「打坐冥想」「厨房做菜」有着相同的疗效。
「一个另类,一个孤独的另类艺术家。」在《美食之路》重版的序言里,陈晓卿这样评价道。他曾向心理学家陈立请教过罗朗带给他的兴奋和困惑,陈立回答,其实所有艺术家都是心理不健全的人,他们在意自己的表达,但不一定在意你是否能懂,因为并不是所有客人都是「精神科大夫」。
罗朗从未以「艺术家」自居,对「所有」这个前缀也持保留态度。但他欣然接受一切以真诚为前提的评价。食客、同行、团队接受采访,他再三强调,你们说心里话就可以,骂我或者说不好都行,只要是真话我都接受。也许他提及的人类学家维克多 · 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这本书中的说法更接近真实,「先知和艺术家都有着成为阈限(liminality)人、边缘人或是临界人的倾向。」当他们把自己抛向生活的边缘时,艺术的张力便产生了。

徒弟唐久祥注意到,罗朗每次从香港回来,心情都不太愉快。这是一个瘦瘦的四川男孩,话尤其少,总在厨房默默忙碌。
2018 年,经闫祺介绍,18 岁的唐久祥开始跟着罗朗学习做菜。5 年来,他们住同一栋房子,罗朗一直试图把他往「家人」拉近,但不管关系多近,小祥总是会保持一点距离 —— 罗朗始终是师父、是老板。罗朗后知后觉地发现,他和小祥的关系反而是所有人里最好的,从来没发生过矛盾。「他知道我的位置在哪,我也知道他的位置在哪,我们互相尊重,也许这样是最好的。」
前不久,又一次和闫祺发生矛盾后,罗朗和小祥有了 5 年来唯一一次「越界」的对话。
小祥:我知道你每一次从香港回来都不太开心。
罗朗:对。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小祥:可能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
罗朗: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我的要求不是很难达到,只有愿意和不愿意。而且我要求你们做什么,不会是乱要求的。我要你们做的,我也会在你们身边一起。
小祥:我能理解。
罗朗:你理解,那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好。我把这半辈子的精力、时间、钱和所谓的创意都投在了这里,也就是说投资在了你们身上,如果你们无所谓,我就觉得我这是在浪费生命。
小祥:我完全理解。其实去香港之后(注:2022 年 10 月,因为香港的一个活动,小祥从广州去到香港,待了五六天),我更能理解你一个人在中国生活是什么感觉了。在香港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人沟通,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去哪,所以就不出你家。其实有时候,我希望你在餐厅时间少一点,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孩子。但我也希望你在这多一点,这样我们也能多学习一点,很矛盾。

罗朗在为甜品「竹叶青」尝试竹签位置。唐久祥是工作中的得力帮手,时常独当一面。
广州并非罗朗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在百年洋楼里做饭,想象中很惬意,实际上一下雨就漏水,我认为广州只有两个天气 —— 热和雨,每天夜里一下雨,我就得起床拖地。」他曾在「一条」的采访中这样说道。很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问自己这个地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年一年过得那么快,没房、没车、没结婚、没小孩,也没赚到什么钱,杂志报道和奖项一大堆,但都跟这个餐厅无关。每次和堪萨斯的父母通视频,他们头发越来越白,脸上皱纹越来越多,他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渐渐老去,失去了那么多,错过了那么多,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但真到了做决定的时候,罗朗总是选择留下。2020 年春节,疫情刚开始时,罗朗的爸爸打来电话,老人家有预感,疫情一两年怕是过不去。他对罗朗说,你要么现在回来,要么就回不来了。罗朗想的是,如果我走了,我的员工怎么办,我的狗怎么办?
他的手机里存有一段视频,拍摄于不久前厨房的某个角落:一只蚂蚁拽着另一只已经死去的蚂蚁,想要把它背回巢穴。罗朗说,这是这段时间最打动我的事。

他总是对「边角」叙事格外感兴趣。新疆、西藏、陕北、黔东南,过去十余年「在路上」,罗朗去的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手工炒米、传统藏包、街边小贩的烤洋芋、土窑洞灶台上的黄馍馍,那些远离中心议题的食物也一一被他带到了朗泮轩餐桌上。
「因为我在中国就属于一个少数民族。」罗朗这样解释他对边缘地区文化的格外关切。2021 年拍摄《厨房里有哲学家》期间,他带着小狗拉姆一起,多次被酒店拒绝接待。「有时候外国人可以入住,但狗不行,有时候是狗可以入住,但外国人不行,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入住。」在中国兜兜转转二十余年,时不时地,他还是被当作「奇观」看待,更有甚者,当面询问他怎么看中美关系。


「牧民餐桌」由牛肉、藏包、糌粑构成。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林卫辉的视角里,罗朗没有汉族沙文主义的意识 —— 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哪一种文化天然地比另一种文化更值得书写(他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如今,民族文化本身的多样性越来越像种植园里的苹果,现代社会在刻意给不同价值赋予不同等级,其中一些优于另一些。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传统都一样宝贵,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完整地代表中国文化,因此,每一份菜单我都会融入中国各民族的特色菜式,因为我想让它们被人们看见。」) 。这是林卫辉眼中罗朗和朗泮轩的可贵之处,「如果他们不去做的话,那些食物永远就只在犄角旮旯的地方,越来越边缘化,现在他们所做的便是不要让它完全边缘化,因为边缘了就会消失。」
对于诸如葵菜这种已经消失在中国现代种植体系中的古老食材,罗朗也试图伸出手去,摸一下历史灰烬下的余温,然后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余温叠加起来,一起呈现在大众面前。克洛德 · 列维 - 斯特劳斯曾在著作中呼吁,任何文化都不应该消失,不论是在亚马逊流域,还是在塞纳河沿岸。和这位人类学家一样,罗朗也有一个犹太姓氏。他小时候是个胖小孩,少时随着军人父亲迁徙,经常遭遇欺凌,自然而然地对弱势一方有更深的连结与温情。
即使最讨厌的蚊子,拍死它们时,罗朗也会有片刻的感同身受:每次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时,都会忍不住问为什么,为什么生活要这么对我?可能蚊子的感受也一样,我刚刚在路上走得好好的,就被人拍死了,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2022 年秋,罗朗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始攻读人类学硕士课程。他对高克宁的说辞是,自己的知识体系不够用了,而且还想进行更体系化的田野调查,所以要去读书,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彼时,《厨房里有哲学家》刚上线不久,很多商家找到高克宁询价,罗朗不为所动。在那之前,他发现胃里长了一个瘤,估算了下,如果是胃癌,最理想的情况不过 5 年。他决定做一些完全自私的事,不为钱,不为团队,不为其他任何人,纯粹只因为「我想要去做」。
读书的念头由来已久。在美国时,他并非一个好学生,高中差点没毕业。这些年,他一边做菜,一边埋头研究各种前人古籍,时常惊讶于他人的渊博:他怎么知道这个?又在哪里发现了那个?他去图书馆找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意识到系统性学习的必要性。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罗朗说,如果我的生命真到了晚上,现在我还只听了半句真话。他不想成为那个在晚上遗憾离去的人。

甜品「寺洼鬲粟」。

黑谷、黄谷、糯小米与野菊花。

秋月梨与甘菊。

自制酸奶与蜂蜜。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学生生活和想象中相差无几。「很多已经发生的、我熟悉的事,现在要重新认识和了解,而且是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角度。」罗朗正在学习的人类学家维克多 · 特纳有一个「Thrice - born」(三次诞生)理论:第一次诞生,我们出生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时刻,它塑造了我们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法;第二次诞生发生在我们离开熟悉的地方来到陌生异邦时,既有的一切常识被打破,我们成了一个新的人;第三次,是当我们用这个新人视角再回头去注视那些熟悉之物时,发现原来它们也蕴含着那么多独特之处。罗朗正在经历这个过程,觉得甚是有趣。
在香港的生活也规律不少。他每天按时吃饭,饮食健康。胃里那个瘤奇迹般消失了。从此,罗朗和周围人立下了一条新规矩:我可以和任何人开会,但以后只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

在朗泮轩,罗朗不怕客人说不好吃或吃不懂,最怕的是四个字 —— 慕名而来。「一听到这个我就想跑。」
鲁西西很少说话,她到这就是找寻安静的。每次推开朗泮轩那扇木门,世界便一分为二:身后是十足喧嚣,眼前是一贯宁静,像伊朗导演阿巴斯 · 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电影,每一帧都是一种静态的流动。
作为「和每位员工都说上过几句话」的常客,西西记不清来过朗泮轩多少次,感慨于这里始终如一。「从人到这墙、这桌子、这杯、这茶,到楼上那个小天台,所有风格是如此一致。」她从小在北京胡同长大,过去 20 年里,那里各种拆迁改造,现在什么都不剩了。「中国什么东西都变得太快,所以我觉得变不是件好事,能一直不变才难。」
西西在广州做跨境电商生意,生活里一大爱好便是体验各式精致餐饮,每年花费不菲。她发现,绝大部分精致餐饮都是一门生意,朗泮轩的特别在于,它首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空间,然后再是一家营业的餐厅。

朗泮轩会客厅内的榆木桌与旧瓷片磨制而成的甜品碟。
但广州是否有足够适合朗泮轩生存的土壤,这个问题是存疑的。鲁西西来广州 8 年,评价这座城市的食物价值观是「平靓正」。粤菜根基太过强大,认可贵价食材,身边钟情新式餐饮体验的年轻人也不如其他大城市普遍。「这不是老一代的问题,很多 90 后、00 后都如此。」从她的视角看来,沙面这个游客集中的区域,也并非目标消费群愿意前往的目的地 —— 太过堵车。她住在天河区,距离并不算远(大约 20 公里),每次来回都两小时起。
在这个吃食材的城市,罗朗倾注在普通食材上的巧思,有多少食客能欣赏得来,西西也在心里暗暗打了个问号。对于精致餐饮,她有一套自己的评分标准 —— 过三个月还能不能记得。去年秋冬菜单上的「龙珠记」她印象尤为深刻:猪肉经腌制、烟熏、低温慢煮后,用彩椒和烤过的菠萝包裹成小球油炸,再加入山楂和乌梅调制的酸甜汁调味。就像朗泮轩给她的感觉一样,这道菜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内藏玄机 —— 她想起了咕咾肉、糖醋里脊和很多儿时的美好记忆。

甜品「果脯」,一杯岩茶与二三干果,重要的是独一无二的食器。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食物是否美味,关乎口味、偏好以及自我投射。西西记得,当时一起来的有位佛山女孩,直言「龙珠记」是她最不喜欢的一道。「但我的偏好是被满足了的。」西西强调。
在她的视角里,以广式肠粉为灵感的「江海丹青」是最能代表罗朗的一道菜:黑色竹炭面和白面制作的软糯粉皮,裹以蟹肉、马蹄,再用自家熬制的蟹油、蚝油调味和点缀,以卷轴状呈现在白瓷之上,本身就是一幅写意的水墨画。罗朗似乎有一种天赋,很是擅长把毫无关系的几样东西,在脑子里揉一揉、捏一捏,就能输出一种出乎意料的新东西。有好几次,西西见罗朗走着走着,突然在一处停下,掏出手机开始拍照。「你在干嘛?」她不解。罗朗扬了扬手机里近 3 万张照片的相册,「不然我的灵感从哪来?」在外面,西西见过不少人学他的菜,那些餐厅都比他的有名。她有些为他不平,「当这个世界的 leader(领导者)是非常难的,但是当 follower(追随者)很容易。」她自己也曾尝试做原创生意,最后以失败告终。朗泮轩的菜式研发期长,售卖期短,用生意人的话说,投产比是极低的。「因为知道这事有多难,所以我特别欣赏这种精神,我做不到的事,有人替你做到了。」
高克宁也在朗泮轩找到了某种投射。中途退出后,她和罗朗一度闹到不愉快。后来在某个活动上遇见,罗朗问她,还要不要继续一起合作。最终她还是应了下来。但显然,朗泮轩的营收连一个合伙人都养不起,如今,高克宁还做着一份全职工作。「每次想到这个地方还跟自己有关系,还能跟着他一起成长,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她说,朗泮轩人来人往,真正对这个地方投入感情的,一定是同类人,「它会帮你筛出很多同类。」

楼顶菜园的西红柿开始由青转红,昭告着天气变暖、春季到来。
去年秋天,鲁西西短期内又一次来吃秋季菜单,开餐前 3 小时,罗朗得知有客人重复来了,当即换了她一人当晚所有菜式,忙坏了整个厨房。西西明白,这种对客人细微感受的照顾,一旦规模化之后是做不到的。私心上来讲,她觉得朗泮轩开在广州挺好的 —— 因为能常来。但她也说,我希望这里永远订不上位,因为罗朗和他的菜值得被全世界看见。
下午 5 点,西西爬上那个被她称为「sanctuary(避难所)」的天台。罗勒、旱金莲长势喜人,西红柿也已开始挂果,蜜蜂在莳萝上小憩。偶尔,罗朗也会上去呆一会儿,看天空,想事情,望着鸽子飞来飞去。小狗拉姆(Lhamo,藏语名,意为「女神」)和战罢(jam pa,藏语名,意为「慈爱」),就在一旁陪着他。

和罗朗的采访原本定在晚宴前夜。那日,他忙得脚不沾地,晚上 9 点,还坐在厨房一把绿色的小木椅上,一朵朵处理两种不同野菊花的蕊,神色始终凝重,像大考在即的学生。晚宴当日,他早上 8 点到达餐厅,回到家时已是凌晨 1 点,站了 17 个小时,腿早已没了知觉。隔日,上午 11 点,他出现在朗泮轩,带着一身浓得化不开的疲惫。
几杯老白茶下肚,疲惫消散了些。目光所及的每件物品,他都娓娓道来背后的故事:眼前这张榆木长桌来自河北的一扇老门;桌下的地毯是从新疆喀什背回,为此错过火车,坐了一趟 8 个小时的站票到阿克苏才能转车回北京;墙角那张棕色沙发,在深圳的私房菜馆就跟着他,大半本《美食之路》都在这上面写就,写到凌晨几点,直接在上面睡过去。

朗泮轩餐厅一角,斑驳墙壁上挂着他收藏的描绘着徽派建筑的油画。
这座建于 1924 年的老洋楼,到明年就是真正的百年建筑了。5 年的房租合同也将在明年 9 月到期,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要在这里继续。百年建筑自有妙处,但也有其局限 —— 不能出现任何明火 —— 罗朗对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源于兴趣,另外也有现实考量:如何在不做炝炒的前提下,通过蒸、炖、煎、烤传递中餐的美与价值,古籍里有一部分答案。
到期之后怎么办?罗朗轻轻蹙眉,「先做着吧。做一天算一天。」采访中,他曾提到朗泮轩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原来生活还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希望,只要它还开着,希望就还在。
成都、深圳、广州,罗朗曾在多个城市实践自己的食物哲学,但没一个获得过世俗意义上的认可。过去三四年,高克宁眼见着罗朗瘦了,两腮深削下去,鬓脚开始爬上白发,她知道他内心始终是煎熬的,「毕竟他做的事情并没得到它应有的价值认可,很多在他看来不如自己的人、餐厅,却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社会影响力。」

罗朗与马。
我们疑惑,为什么一定得是中餐呢?他会画画,文字也好,还有半屋子收藏,任何一项单拎出来,都是比食物门槛高得多的艺术门类 —— 也轮不到人人都来指手划脚一番。当然,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变得很「成功」。
罗朗的回答很简单:大概还是通过食物能更好地表达自我吧。
或许还有一层天真的好奇。他脑海中存有诸多关于食物的奇思妙想:比如用蔓越莓汁、桂花粉做「线香」,用可可粉和黑芝麻做「瓦片」,用细长的烤饼干做占卜的「签」。高克宁曾评价罗朗,他有两套并行的工具,一方面像学者已经具备一套成熟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看中餐又像个孩子,有一种饱满的好奇,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他不会觉得理所当然,总有新的探究与发现。
在那之下,还有一丝挑战的意味。「挑战人的既有想象」这句话,罗朗在不同场合,一遍一遍提起。
但最根本的,如他所言:你可以从饮食理解到他人的一切,他的文化、他的信仰、他的恐惧,他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罗朗从不把食物只看成是「物」,而是把它们和「人」联系在一起,总是透过「食物」看到「他人」以及「自己」。他对食物的礼赞,也是对人的礼赞,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勤勉、人的无穷想象力。

第一次来中国时,罗朗 18 岁,今年,他 43 了。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快要赶上在美国的时间。做中餐有改变罗朗吗,又或者罗朗有改变中餐吗?高克宁摇摇头,他们谁也没改变谁,「只能说他跟这些东西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沉浸。」
「In the beginning culture does beguile us, but nature gets us in the end.(一开始文化让我们着迷,但最后还是本能说了算。)」罗朗引用了美国作家约翰 · 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一句话。眼下,他对怎么把侗族牛瘪做成另一个样子抱有极大热情,但最爱吃的还是沙拉、三明治、肠粉、银针粉之类寻常的食物。

平凡的食材土豆,经过炭烤在表面形成黑色的外壳,内里却金黄、稳妥、软糯,成为西南地区人们冬日的慰藉。

烤土豆。
但高克宁也欣慰地注意到,罗朗会跟人说上点客气话了。尤其对于一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他内心是感恩的,以前并不习惯表达。闫祺也说,罗朗越来越成熟了。过去,她的妈妈常叫他「罗三岁」,做事想一出是一出,带着他们也能把火车坐过站。「现在各方面都靠谱一点了,也愿意面对和正视自己的错误,虽然说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吧,但会去改。」
始终如一的还是烹饪上近乎执拗的完美主义。他不改菜 —— 很多东西都在脑海里过了上千遍,他不轻易接受改动。「如果别人说这个更好卖一点,那就让别人去卖吧。」高克宁说,这就是罗朗的态度,他的生活方式,他生活的一部分,过程中如果有人懂了,能产生另外的附加值自然好,如果没有,那他就不做了吗,或者说,他就不生活了吗?
林裕立说,罗朗让广州的餐饮业态更多元了。
林卫辉表示,朗泮轩可能会有曲高和寡的问题,但我们也没必要杞人忧天。
鲁西西说,罗朗做到这个地步,从经济效益上是不合理的,但他这样做了,真正受益的是我们。

朗泮轩位于广州沙面北街 73 号,由红色木门进入,走廊尽头步行木楼梯至 4 楼,到达天台,木门后就是餐厅。
房子明年到期的事闫祺也知晓,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你把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其他都是恩赐。」
高克宁现公司老板是朗泮轩早期四位投资人之一,曾直白地问她:你觉得一个人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这事儿靠谱吗?你要知道人是最不可控的。高克宁说:「可能我确实判断错了,这事根本不在于商业价值,它有它自己的价值,并且会越来越凸显 —— 因为它的独特性很强,取悦市场的标准都差不多,最后就趋同了。朗泮轩不取悦,它就能保持自己,只要活着,它就会越来越独特。」

楼顶的天台上,罗朗种下的第一个植物是竹子。「竹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它都能生长得很好。来到广州后,所有人都说在这里开这么个餐厅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人们的要求非常高……我会对自己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像竹子一样,哪怕被种植在一个看起来不理想的地方,也能够茁壮成长。」晚宴菜式「竹叶青」卡片上的一段话,某种程度也是他的自况 —— 他并非对现实毫不知情。
他不会放弃的,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这是「很有马背智慧的一个人」,认定了一个事,就会一直做下去,碰到任何困难都不松手。过程中痛苦是他的,快乐也是他的,他徘徊在快乐与痛苦之间,留下一道道满载故事的味觉体验,宛若竹林投下的一地清幽。

「竹叶青」是一个竹笋棉花糖。


罗朗撰写的菜品故事。
18 岁,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中文,罗朗学会的第一个成语是,别怕慢就怕站。采访结束后次日,罗朗发来当日菜式的数张照片。这是他第三次做这套菜,隔着屏幕也不难看出,比第一次出品更为细腻、优雅,像一首首写给春天的小诗。「Getting closer to perfect(趋近完美)。」这个完美主义者终于松了口。
今年 9 月,罗朗就满 44 岁了,他时常问自己「来回中国 20 多年,这些时间都去哪了?」偶尔,他会疑惑怎么会在美国驻华大使官邸待上 3 年 ,开玩笑称那几年像老了 20 岁似的。但如果重来一次,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那个选择。「因为你做了什么,才会发现不想做什么,或者清楚你更想做什么。」正如哲人所言,你必须先走上万里路,才会发觉不必出门。
那么,现在接近理想的生活吗?他摇头 ——
「这个生活方式理想吗?不理想。喜欢吗?不喜欢。有意义吗?非常有意义。」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像等候多时一支终于可以射出的箭。罗朗说,事实上,生活更像一场不断的谈判。就像骑马。「当你在马上时,你正在与一个身体、意志比你强壮得多的个体对话。你得知道它的感受,它也会通过你的身体来感受你的感受。你紧张马也会紧张,你焦虑马也焦虑,你开心马也快活,你若对它用蛮力,马就会摔断一条腿。这有点像生活 —— 它给予我们一些东西,好的或坏的,我们做出回应,然后,生活会根据我们的回应,再给出新的回应。」

在海边余晖下的罗朗,骑着白马 —— 这是他近来一直想做的事情,也是他觉得最「没有」自我的时刻。
采访里他总有妙语,像溪流里时不时跃出水面的鱼,闪着智慧的银光。但它并不指向事物的本质 —— 因为生活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做出反应,马的反馈则直接得多。
罗朗明白。所以他选择先跨上马背,集中、放空、任意识流淌。在某个时刻,魔法发生了:时间消失,空间消失,中餐与西餐的界限消失,痛苦与快乐也都一并消失,最后,自我也消失不见了。骑手和马成为一体,罗朗与万物同在。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170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