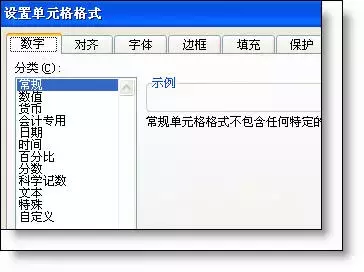我的日语学习历程分享!漫长的日语修行之路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不是日语学习的计划以及相关的问题以及实操性的东西,主要是给大家讲述一个漫长的日语学习过程和经验,怎么说呢,希望在兼顾趣味性的同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

仔细回想,初学日语应该是1995年。
1994年,也就是我十四岁那年,从云南回到上海参加中考,结果惨败,原因之一是教材不同,另一方面是有些轻敌。我念了一所职校的中专班(有点诡异,明明是职校,文凭倒是中专),刚进校时不明所以,只知道所学专业叫作“中层管理”,过了一阵才发现,什么中层管理,就是商场营业员。尽管不是个心怀大志的人,我还是有些郁闷。好在邂逅了日本漫画,足以排遣一切负面情绪。云南小镇的孩子没见过漫画书,突然接触到《尼罗河女儿》《东京巴比伦》乃至后来的《幽游白书》《不可思议游戏》《灌篮高手》,简直像一头扎进了一片异文化的汪洋。
升二年级的暑假,被同学带着报了前进进修学校的暑期班,用的教材是《标准日本语 初级 上》。老师多半是某大学出来兼职的。暑假过完,职校的日语课也开始了,日语老师由政治老师兼任,他以前在日本留学,和许多日本归国男士一样,从发型到面目都依稀日化。
至于职校为什么学日语,可能是一种潮流。我们班确实有学这个的必要,因为每个班级有对口也就是毕业包分配的商场,我所在的是“八佰伴”班级。
印象中,学校课业轻松,除了上课都在看漫画。大部分是和同学借了看。也去学校图书馆,在那里偶然翻到一本没有封皮且缺了前十页的小说,觉得“哇小说还能这么写”,深受震撼。还书时请管理员查了才知道,书名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作者叫村上春树。

我当时不知道村上是个那么有名的作家,也没想到,对他的阅读将伴随我一路。
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了村上的五本小说,在福州路的书店没能买全,又写信给出版社,他们寄来读者服务部的印刷品,长长的书单,从中找到了我要的,通过邮局汇款,终于集齐。
职校二年级开始穿插实习,去过好几家商场。三年级,进到上海第一八佰伴,此后就和正式上班差不多,只不过拿的实习工资。(我的两本小说里,程勉、莫凡,都当过营业员。)
那次暑期班之后没再继续报班,买了标日后面三本书,开始自学。方法很简单:每篇课文先听一遍录音,试着看自己能听懂多少,然后查单词,学新的句子,跟读。最后把课文背下来。
这种学习方法非常笨拙低效,我恰好比较有时间——商场做一休一,一个月有十五天属于自己——又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娱乐。再说了,我喜欢的作家用日语写作,没准哪天能读懂原文书呢。当然了,读原文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深想。更大的动力是“可以看原版漫画”。
在班级里公认“日语好”给我带来一项便利,被分在文房四宝中国字画柜台,顾客大多是呼啸而来游弋而去的日本旅游团的老头老太。因此多了练习口语的机会吗?并没有。价格有标牌,而且我很怕开口。最多的情况是,顾客指着小幅山水问:“印刷的吗?”我答:“不,是画的。”
工艺品部门挺神奇的,有种类似友谊商场的气氛,不那么商业。部门领导更像个文人,有一次还搞了西安碑林拓片展。价格昂贵,当然没人买。我被分去拓片展,对着三面墙的黑底白字枯站一周,实在百无聊赖,其间构思了人生第一篇小说《花魂》,写完后投给《科幻世界》,拿了当年的“少年凡尔纳奖”。

我作为小说作者的序章尚未真正开始,闲时构思小说,同时继续缓慢地学日语。除了背课文,完全不钻研语法,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如今,朋友学日语遇到什么语法问题来问,我都会愣一下。
1998年的春天,实习加正式工作,在商场待了快两年,相当厌倦。当时正好有个在公司上班的机会,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和想象的不太一样。九十年代的私人老板喜欢下班后带着下属社交,一心认为是“为你好”。我太小了,只觉得那些吃喝局极其无聊,一周就辞了工作,去了一家报社。老板语重心长地和我谈,大意是“你以后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记得我还哭了,边哭边说,可是我想写东西,在这里工作根本没法写。
就这样,以写作为理由而跳槽。结果报社是个骗局,唯一的收获是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当时家里经济情况并不好,我这么折腾,父母当然是忧心的。他们觉得放着好好的八佰伴的工作不做(商场月薪一千出头吧,在那个时候和小白领差不多),为什么要这么不靠谱呢。和我因为漫画结缘的职校朋友帮忙说话,最后家里同意让我去念全日制的自考班。其实早先上班的时候考了华师大中文系自考的几门课,可惜中文系没有全日制,我最后按时代的潮流选了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一年学费四千多,学制两年半。
后面一段时光非常穷,同时快乐极了。自考班要十月才开学,我尚未满十八岁,整个夏天,每天骑车到上海图书馆,看书,学日语,写小说。寄存自行车五角钱。罗森的饭团两元。两块五就是一天的开销。上图楼上的外国期刊阅览室有日本杂志,拿出来瞅两眼,太多不认识的字,于是继续看我的课本。

大学期间开始当家教。按理我一个连高中都没念过的自考生,好像不太适合教小孩。中介是个戴眼镜的男生,忘了怎么聊到了《科幻世界》,他听说我发表过小说,欣然同意。继续骑着自行车晃悠,去学校,去虹桥的学生家。在《科幻世界》又发了一两篇,没有更大的水花。倒是日语那边,付出便有结果,吭哧吭哧念完了标日四本书,报了个二级的考前培训班。也是这个班才让我知道得买本《新明解国语字典》,不能老看汉语解释。考前班是题海战术的路子,顺利考了二级,以为自己日语很好了,其实刚摸到门把手,连门都还没开。现在想来,年轻就是好,无知又无畏。
那会儿市面上开始流行日剧的盗版vcd,《悠长假期》《沙滩男孩》等,在同学的租屋看了一堆。仍然需要字幕。从来没想过靠日剧学口语和听力,看剧就只是看剧。
2000年,大专自考那边还没念完,有个中日合资企业的面试机会。该公司想找个会日语的文员,已面了几个日语系应届生,我毫不知情。去了以后有笔试和口试。我第一次和母语是日语的人对话,紧张自不待言,表现应该挺拙劣的。也不知怎么就被招进去了,可能因为我提的期望薪值比较低。
写字楼的一楼有个投币饮料机,可以买热果珍或可可,当时显得先进。有一次我正在等饮料出来,看见部长过来了,他是个热爱玩单板滑雪的年轻人,也就三十出头,我还不满二十岁,把他看作叔叔。一紧张便说:“我可以喝果汁吗?”那边莞尔一笑,纠正道:“你要喝果汁吗——你是想说这个吧?”

也许有人会说,日语二级就这水平?没错,考级和实际应用之间的鸿沟,需要时间填补。副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中文不错,我一直无视他的普通话,总是用日语回答,他内心想必相当无奈……总之我就此练起了口语。
该企业的主业是某种日用大型机械,图纸都是日语的,中方技术员经常来问我某个词的含义。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我决定做一本速查手册,也可以说是字典。整个过程远没有《编舟记》主人公的趣味,每天从图纸搜集尚未收录的词,和副部长确认中文含义,手写抄录。对,是手写。日方领导们各有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就两台,是公用的。我的“不务正业”当然不能占用公共资源,做字典用的也是边角料时间。
大概花了一个多月,手写字典完成。就在我桌上,和技术员们说了可随时取用,不过他们还是习惯口头询问。做字典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专业词汇,我看一眼都能条件反射地说出对应的中/日语。偶尔想不起来,便拿出册子查看。
日本总部管研发的部长来出差,看到那个本子,笑了。他后来给我带了一本术语手册,原来日本总部有人做过,比我的版本更详细,而且是印刷装订成册的……可想而知我有多窘迫,但做字典的傻劲似乎让此人十分感动,几年后,当我养了三只猫,他特地从日本带来一块双层塑料垫,是搁在猫砂盆前给猫蹭脚掌砂粒的。
中间换过工作,在软件公司待了小半年,又到原单位新建的研发中心,总算“专业对口”地做起了网管,薪水也终于涨到了三千多。那是在2002年。其实我在学校学的是老掉牙的编程(C语言之前的古老语言们),全无网管的专业技能,连网线头都是领导H手把手教着做的。
H是个有趣的理科男,爱穿绿色系的衣服,明明是机械专业却精通局域网建设。他不谙中文,需要一个人帮他和中方工程师沟通,所以愿意教我从头学起。我除了管局域网,就是给他当翻译,跟他一起开各种会。口语真正进步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级也考出来了,我以为自己学日语的过程算是结束了(多么天真)。
第一本村上原文书是H回日本出差后带来的,短篇集《电视人》。1993年的文春文库一版一次,距离发售将近十年到了我的手边,全新的。可能买短篇集的人没那么多?记得是查字典读的。最后一篇是《眠》,早就读过《象的失踪》里的译文,读原文还是很喜欢。
工作不忙,我开始在网上写小说,更新时间都在上班期间,每天一千来字。不用大纲的写作方式从此伴随了很久,后来将证明这是个需要改掉的坏习惯。
2004年离职去深圳,自考还剩两三门,我尚未拿到大专文凭,有的只是一张日语一级证书。在某家装杂志干了几个月,觉得形势不太妙,上网找工作。记得好像是在“前程无忧”网站看了一圈,深圳的日企多是关外的工厂,让人望而生畏。我改为在论坛搜寻。还真找到一条招聘信息,是一家免费日文资讯杂志,说要招编辑助理。我打了电话,那边让我直接去面试。
去了一看,商住楼里的两室,屋里挤了几个人,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是快要溢出来的印刷品。那氛围完全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杂志社。虽然觉得不靠谱,也没有别的选择,聊了聊便答应入职。老板K是个留络腮胡的大个子,中文口音很怪,笑起来声音洪亮。要等到后来熟悉了,我才会知道,他曾是《周刊现代》的记者(俗称狗仔队)。
在杂志社待了两年,时间既快又慢。一期又一期杂志出刊前的加班(最忙时两天两夜才睡几个小时),空下来便和同事们吃遍全深圳的日料店——几乎所有店家都是我们的广告客户,部分广告费折算成饭券,不吃就浪费了。公司“不拘一格用人”,美编并非科班出身,技校毕业的四川姑娘,上一份工作在凸版印刷,准确说来是个熟练排版工。但凡美编姑娘认可的日料店,总是没多久就关门了。K说,那是因为太“中国口味”。
杂志社聚集了若干不走寻常路的日籍员工:曾浪迹南美的叔叔,精通IT,负责公司网络和杂志邮寄事务;在香港拉广告的是K的合伙人,为了省钱,借住在某教派的便宜宿舍里;曾在时尚杂志《Olive》担任编辑的女士,带来她的两个跟班,此人集合了所有白领影视剧恶领导的一身毛病,我不堪其凌虐,提辞职,老板劝阻,每天下班后拉着我谈两个小时……中国同事评论道,你辞职比别人离婚还难。
不用说,拜我们超级唠叨的前记者K所赐,口语的进展一日千里。
在杂志社还遇到了我至今的好友O。他曾是K在日本的“师父”,被K请来做外援,比我进社晚,后来在中国待了近十年,中间也写过小说,如今在东京继续当采编一体的自由职业者。
我看着杂志社从商住楼挪到特区报大厦,事业拓展,公司外表变得光鲜,然而并没有从工作产生归属感。其间终于艰难地考完了高数和政治(最让人头疼的两门),拿到了大专文凭。2006年,我辞职回上海考研。报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距离最初学日语,11年过去了。
到今天我都感谢上外,因为它是一所公平的学校,可以让大专自考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研。
为考研做准备的半年,在虹口租了房子,上午学日语,下午补习政治和英语。听了一个朋友的建议,报了政治英语培训班,后来十分感谢这份建议。至于学日语的部分,就是按照上外列的书单,把上外课本乃至几本语法书啃一遍。上外的5-8册虽然有些“老”,编排非常合理,也有许多好文章可读,让我把自己的弱项都补了一下(最主要是阅读词汇量,毕竟日常口语的词汇有限)。另一项自我训练是翻译《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栏目,每天一则。
我逐渐树立起对未来的明确预期,想要当引进书的图书编辑,不行就当个译者。记得是在论坛上认识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李建云。我直到离考试不久才做了历年考题,一做就慌了,问李建云,怎么还有古文?她说,我们大学要学的呀,不过分不多的,你可以放弃。
古文一共十分。十分那也是分哪,于是我又花了一周时间,“硬”学古文。
同等学力需要在在四门考试之外加考两门专业课。我一看到加考的考卷就知道了,上外没有刁难同等学力考生,卷子比专业课的两门简单。真正让人犯怵的是专业课的写作题,我作为一个写过几篇日文报道的人(仗着有同事改稿),完全没碰过所谓作文,临阵磨枪做了几篇,发邮件请O修改。他一向是认真的人,给我逐字逐句改了。我再据此研究自己的不足。
笔试后还有面试,进了房间有点懵,我以为面试嘛,就一两个老师,没想到屋里坐了七八位,大部分一看就是老教授。不知为什么有种花果山大小将领的感觉(并不是说老师像猴儿,只是我的心情如小妖拜山)。结果因为太紧张,张嘴便是日语闲扯,按前领导K的风格一路扯开去,严重离题……
就这样,考上了上外的公费研究生。上课按部就班,没觉得特别有趣。读研期间接了翻译《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的活儿,第一次翻译,有些句子还是僵硬,编辑用铅笔圈了,把我喊去办公室逐条现场改。
这里插入一段关于阅读的回忆:在深圳时,办公室有间图书室,里面是K和同事们的藏书,好几个书架,量着实不少。然而我压根儿不读书,主要是工作太忙了,无心也无力阅读自家杂志稿件以外的文字。有个兼职记者是爱写东西的主妇,来办公室的时候和我聊起她特别喜欢梨木香步的作品,借了我一本《后院》。梨木本来就是语言特别好的作家,又有哲思感,一读之下,相当震撼。
研究生期间,我还是没读多少日本小说。欧美翻译作品多好看啊,相比之下更愿意读哪些。初读《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的时候甚至有点嘀咕:直木奖这么清浅啊。
清浅欢快也是一种功力,那时我还不懂。正好自己写小说愈发带劲了,写了短篇《人字旁》等,长篇《月光花》,然后是《甲马》的初稿。精力放在写,读便有限。此外,论文花了不少时间。毕业论文写的是《谷崎润一郎<细雪>的叙事学研究》,上外要求论文用日文写,我向来话痨,要求三万字的论文哗哗写了五万出头。
论文毕竟是大事,我又找当时正好来了上海工作的O掌眼。本意是请他看看错误的句子帮我挑出来,他居然给逐字逐句改了。我重新细读,研究他的修改,深感沮丧。他安慰说,你的日文写作比K强多了。
日本的周刊对记者的文采要求不高,重点是能挖到料,K的水平我也清楚,苦笑,心想这算是夸吗。
总之,经过O修改的漂亮文章,经过论文审读组S老师一读,当即以为我是抄袭。他直接提出质疑,我便解释了,又发了带有修改痕迹的那一版文件给他。他说,你这朋友太好了,你得请他吃饭啊!
算得上是“不打不相识”,没教过我的S老师和我成了朋友。他借给我的书都是复印本。通常他买了什么有趣的书,就放在系里的资料室,同时还会复印个一两份给需要的学生传看。就是在S的推荐下,我读了桐野夏生的《有什么》(国内后来译为《又怎样》),写林芙美子的小说。S说,我原来不大看得上桐野,这本却很好。
若干年后,作为编辑,我出版了桐野夏生的《柔嫩的脸颊》,与这时的邂逅不无关系。除了《有什么》,我更偏爱S老师看不上的桐野夏生早期作品。阅读这件事非常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和目标,有自己为之驻足的风景。
S听说我喜欢村上春树,给我找了许多关于村上的文论。在他那里还读到井上厦的遗作《一星期》。读书有时是需要讨论的,看过后和S谈感想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我开始有兴趣读书,为《书城》写了一段时间的日本文学介绍,每次介绍一本书。类似的栏目后来还在《南方都市报》写过。
我毕业没多久,S结束上外的工作回国。他年事已高,回山形休养,照顾老伴。我以为S老师对我“有外挂”的论文是不满意的,没想到他说,在上外这么些年,只带走一份论文,就是我的。后来的几年间,我们偶有邮件往来,直到我当了编辑,有读不完的样书,他仍然热心地推荐我读这读那,其态度一直是严肃的,把文学当一回事的。
2012年,《1Q84》的前两册面世(一开始只有两册,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出了第三本),托人帮我从日本带回。这是第一次,我得以同步阅读村上的新书,感觉很奇妙。尤其是当自己多少写了点小说,读书和思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深圳工作期间去过一次东京,短暂的出差,也是到了2012年,才开始去日本旅游。实际走过当地,见识过风土人情,再来读书,很多感受更加切实。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学外语的人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的影视和书籍资源,出国也相对容易。
从2012到2019年,我当编辑,业余写小说。薪酬方面就不说了,一言难尽。以前虽然跨了几个行业,工资总是随着时代在涨,2006年回上海前大概是7k不到点。新编辑的起薪,业内的诸位想必也知道,落差让人心酸。何况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十年了呢。好处也有,首先是书多,想看什么,可以问版代要。为工作读书是什么滋味,大家都懂,甘苦不能一概而论。最大的惊喜是读到吉田修一的小说,前后两次采访他。关于读和写,从吉田那里也有许多启示。
书带来人,人带来更多的书。从村上读到约翰·欧文,算是顺理成章。O喜爱的高村薰,后来也是我的挚爱。S老师送给我一本米原万里的小说,开启了我对这位才女的漫长追读。吉田修一推荐的松浦理英子,让我颇为沉迷。对《编舟记》的译文一见倾心,找译者蒋葳翻译《木暮庄》,和她成了朋友,因此结识“花之24年组”,从日亚买了漫画《托马的心脏》,在单行本出版34年后迟来的遇见,不减损感动……
为了更好地专注于读写,2019年初离职。纯属偶然,年底开始翻译樋口一叶。我终于发现,学习是没有尽头的,读一叶原文,所谓“雅俗折中体”,用中文说就是“半文半白”,不得不再次努力学起来。用流行语说,“点亮了以后都用不到的技能树”。沉浸在一叶的原文中,如同走上一条陌生的道路,连空气的质地也变得不同。
进入2020年,世界陷入剧变,我在家写小说和翻译,从kindle买了许多日文电子书,有小说也有非虚构,一本接一本读,算是借文字世界维持内心的平静。写信问候S老师,不像以往,回信久久不至。想到S的年纪,觉得应是无缘再收到回信,只能遥拜。在这里写下他的全名,樱田芳树。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若干位给自己带来巨大影响的人,樱田老师于我,是其中之一,光说“谢谢”并不足够,但也只能道声谢。
樱田老师,谢谢您,教会我村上作品以外的阅读的快乐,从此,一个新的世界在眼前铺开。
以上便是关于日语学习的一段非常长的经验和经历。语言的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咋说呢,能够静下心来并且能够及合理安排自己的目标,其实结果不会太差的。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2571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