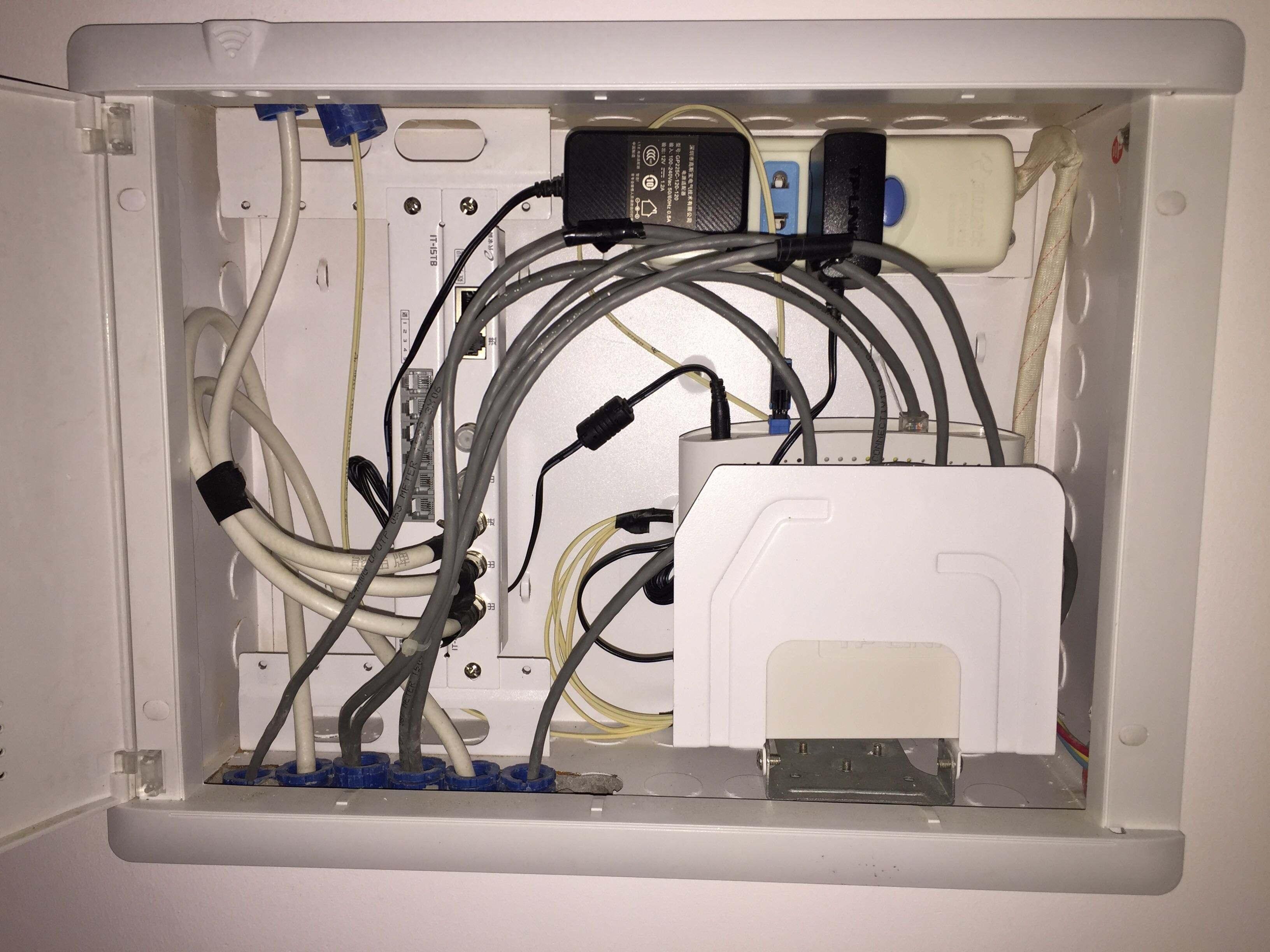三十三【23】
(08-05)那些年的家庭奋斗史
等到我迷迷糊糊揉着眼睛醒来已是凌晨两三点了,父亲并没有喊我,只是周围过往的车辆和人与人聊天的声音吵醒了我。看了一眼父亲,他正趴在手扶横把上用手垫着脑袋补觉呢,我轻轻跳下车不敢打扰他,顺着有灯光的街道寻视着四周。
这是一个面积超大的农贸市场,具体有多大还真没法计算,四面筑有围墙只在南面开了一个进出口。这里聚集了各类批发蔬菜的菜农,他们开着自家的农用车或者雇车将自家货物拉运到这里。各自一个车位算作占聚的摊位吧,车厢后会开一个口子摆出少部分己的商品当做样品,比如用塑料网袋装好的白花花的大蒜或者红,白萝卜。用细绳扎好码的整整齐齐的芹菜或蒜台,豆角之类的。像茄子,辣椒,土豆这类蔬菜一般都会选择用尿素袋子装。如果仔细观察,甚至还可以看到这些蔬菜旁有的会放一个浇花用的小喷壶(或者用矿泉水瓶子装上水,再在瓶盖上用针扎三五个小眼充当喷壶用),那是为了给样品蔬菜降温时刻保持新鲜样貌的一种临时做法。再仔细看还会发现在车厢的某个角落一定会放着一杆大秤或机械台秤(此时节电子秤已可以看到了,但很少被使用,算是未还普及的阶段),之所以是称重货物的大秤是因为来这里的商贩(大多数是菜农,菜贩子比较少,菜贩子都会选择去菜农的地里收购价格更加低廉的蔬菜)都是奔着大量出售的批发而非零售,所以市场上也很少会出现在摊位前买三五公斤之内货物的买家,也算长久以来农贸批发市场的乡俗民约吧?
一定会有后来人好奇为什么菜农们必须选择夜里到这里?白天来不可以么?那我必须要具体解释下原因了。首先,新疆的天气晚上比较凉爽,甚至有些寒冷,一来可以保证蔬菜的新鲜,白天通常气温在二三十度,蔬菜即便是盖上防晒的被子也会有损耗。二来,夜里驾驶车辆比较安全,车少人少交警(虽然那时交警基本上不会查农用车尤其是手扶拖拉机,可为了避嫌驾驶员还是非常谨慎的)也少,而且夜里开车也舒服,毕竟白天公路上行驶迎面吹来的都是热风。其次,农贸批发市场既然称之为市场那么必然就会有摊位,而这里的摊位就商贩们的车子停靠的位置,做过生意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摊位的重要性,就好比买房子买店铺,靠近学校,超市,医院,十字交叉路口的位置都会比较昂贵是一个道理。晚上去早大多是为了去占一个好的摊位,据我所知,通常来讲靠近市场出入口的是非常好的,再就是靠中间的位置,越往里越偏僻的位置生意是最差的。最后,这边前来采购蔬菜的都是各个菜店或者酒店的老板们,集市开始时间特别的早,五点多就开始会陆陆续续有人或骑三轮自行车或开小皮卡前来与菜农们讨价还价了,这种场景一般会持续到大约11点钟的样子,假如这时候还有没有卖光自己的蔬菜,那么就只能等到第二天重新来过了,这时天气还不算完全热起来,商贩们此刻回家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凉爽的。
那天我清晰的记得父亲与好几个前来询价的人暗中较劲,我家种植的辣椒品质还是可以的,偌大的市场里品质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我家的虽然不能说Number one吧,可也是中上等的。父亲刚开始不是很了解辣椒行情,他就让我守着车子他装作买家背着手去其他的摊位去询价,转了一圈后把我家辣椒定价为7毛钱一公斤?有好几个人转了几圈看中了我家的辣椒,可一听价格连连摇头:“再让点,这一车我都要了!”“那老板你出个价嘛……”“对方伸出五个手指”“不行,不行,再加点,我们从十月拉过来的呢,老板再加点呗!”对方只好露出略显遗憾表情扭头走了。父亲始终坚信只要我家辣椒品质不差就一定能买出个好价格,待到那人走后他又对着我嘟囔:“哼,前面有两家那辣椒比我家差哪儿去了,都敢卖6毛,我便宜两毛钱那不亏死了麽……”
之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波询价的老板,也有两个人按照7毛的价格各买了三五个袋子,这更是让我和老爸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父亲还有些开心的给我一块钱让我去馕店买了个超大个的葱花馕饼二人分着吃了。那个看上我家辣椒的年轻人再一次出现在我家摊位前:“大哥,5毛已经不少了,再说我全部拿,给我吧!”父亲也是犟:“不行,7毛钱,要的话就给你过秤!”那个年轻人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那一句:“不是我说啊大哥,这会儿你不买给我,待会罢集了你还得拉回去……”大概那一刻父亲的心理状况是又纠结又抹不开面子又抱着侥幸心理的吧?总之,那年轻人再次得到否定答复后坚定的走开了。果不其然,批发市场的高峰期就就那么两三个小时,过了这个阶段就再也没有什么买家了,看到附近的商贩开始打包装车,我们父子俩也算清楚了,此地不宜久留,父亲一副有些懊悔了吧,有点闷闷不乐的把摆在车边的辣椒往上丢,突然仿佛又想起了什么:“木子,你再去市场里转转,看看刚才那个要买我家辣椒的人还在不,要是碰到了你告诉他,5毛钱全部给,如果不愿意还能再便宜些!”我收到指令飞快朝着市场中心的跑去,那时好年轻,脚步轻盈的像只麻雀,不一会儿就把横着纵着的四道摊位转了个遍,映入眼帘的多是或喜或悲的打包装车的商贩,他们大多数会选择回家,还有很少一部分会选择开往下一个城镇的集市继续“战斗”,还有就是集市附近的小吃摊开始营业了,什么烤包子呀,烤面筋,奶茶等等。从旁边路过,闻着那散发的薄皮包子的味道,使得我直往肚里咽口水,可惜当时很少有零花钱,那些美味是我不能够消费起的,所以只能远观而不能近食之。
回到家后父亲把集市上的经历讲给母亲听,母亲倒也没说啥,只是笑呵呵的骂父亲笨蛋一个:“不管多少钱,看能卖就卖呀,菜又不想其他东西放不了的,装到口袋里的才是钱,拉回来的就只能喂鸡了!”道理父亲当然是明白么,当时的我都可以听得懂况且是父亲呢。那一车的辣子后来真就像母亲说的那样最后真就喂鸡鸭鹅兔羊了,经历路上的颠簸和路上回来的太阳光照射,卸下车时还比较新鲜,没放多久它们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便蔫了。经过这次的“教训”以后,父母亲再出去批发蔬菜很少有往回拉的经历,哪怕价格低,一定会咬着牙抛售出去。还别说,从古至今市场上永远都不缺捡漏的二道贩子,就有瞅着这种机会低价买进高价卖,不过他们通常有自己的门路(或者叫销售渠道),也算是一种依靠市场的谋生手段吧。除了农贸批发市场,牛羊市场也有很多(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商贩),比如某人家里急用钱,牵一头牛去卖,想卖个高价却迟迟卖不出去,等到集市散去垂头丧气的牵着牛往回走,这时总会半路有人拦下他:“朋友!这牛多少钱卖呢?”当得知价格他们百分之一百的会说:“太高啦,太高了,好好说个价嘛!”然后再把手机的钞票在手掌上一拍:“价格低一点嘛,我马上付钱!”卖牛人看到大把的现金内心开始动摇了,这不就是自己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么,心想让一点就让一点吧。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就会被维吾尔族商人以低于市场价格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的价格买到了手。这里绝对没有民族歧视的含义在里面,我只是想说明的是,维吾尔族天生血液里就流传着做生意的天赋,在北疆做牛羊贩卖的多,在南疆各种生意人他们都做。我从不会去评判一个民族的优劣,只能描述他们生活习俗和特征。
写这些个故事一半时我突然想起这段故事与多年前一个叫张培祥(网络上搜的资料)的北大才女写的《卖米》经历很相似,这是我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当时颇有感触(我这人记性不好,即便是多么有感染力的文字我只会感动一时,最多三天就会忘记的很),所以务必要记录下来。我写的内容当然无法与她的文字相比,无论是笔力还是描写形式。毕竟我们处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空间……缅怀2003年逝世 的作者飞花,愿你天堂一切安好。(原本想把原文摘抄于此,怕有侵权嫌疑故而作罢,有想读的后来人在网络上搜索吧!)
总结下养兔,卖豆腐,种菜那几年的家庭经历吧,在我看来那几年父母是拼了命的想给家庭增加收入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可天时地利都没占到。反倒是有点像是猴子掰玉米,看到别人做什么挣上钱了就跟风做什么,等到父母再去重复别人的行业时,那个行业基本上就已经不挣钱了。而父母坚决不会承认我这一说法,也有可能真的像父亲总结过的那样吧,要本钱没钱,要人帮没人帮,即便是机遇摆在面前也只能看着它匆匆溜走吧?当时的他们除了有一腔热血和健硕的身躯外还有我和姐姐,然后一无所有。
如果把家庭奋斗史作为一个章节,那么2003年必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在这一年我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天覆地这词不敢用,有点夸张了,不过焕然一新是可以用用的。这一年我家开始盖新房啦,在建房的同时还经营起养鹅的行当,并且还挣了些小钱。
前面讲过1995年时母亲放羊时看上了河坝那块不化雪的地盘并且请人盖了几件土块房,说实话我已经忘记最初房子的样貌了,只记得好像那房子又矮又阴暗,不过在房子的前面好像用红砖垒过一个不大的小花坛还挺洋气的。
那一年我读小学六年级,姐姐已经升初三了,面对即将升初中的我和升高中的姐姐,对于前些年各种“创业”经历并没挣上钱的父母亲来讲压力无疑是很大的,就连我跟姐姐的学费都很难拿的出。凭良心讲,我跟姐姐从小虽然家庭条件不好可从没有埋怨过父母亲,也从不跟人攀比。我是不想吐苦水的,可写到这里又不禁想起几件小事儿,就也简略的记录下来罢!
时间大约是姐姐刚读初二的那一年吧(2002年?反正就那前后一两年)?有一天骑车放学回家哭着说学校的教务主任在门口拦着她说再不交学费就别来上课了,因为全班就她一个人没交学费了(不知道是多少,三四百块钱?一学期?),当时母亲瞬间气炸了,第二天就骑着车跟着姐姐去找那个戴眼镜的男老师算账,本来在我看来是一件理亏的事,结果性格暴烈的母亲硬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那教导主任给揍了,听她讲把那家伙脸给抓烂了还把眼睛打烂了?反正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母亲的一个原则:我们家不会赖着不交,只是暂时拿不出,凑齐了马上就让女儿带到学校。至于揍那教导主任也纯粹是那家伙说话太难听,因为母亲虽然蛮横却十分讲道理的。从那以后教导主任在没敢跟姐姐提过交学费的事儿了,而且听母亲讲那人在大街上遇到她都是假装没看见躲着走,哈哈,也不知真假。那教导主任在我读初中时还在,只是忘记他姓甚名谁了。
记录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吧(这事儿我好像前面记过了,算了,如果说记过了那就再记录一遍吧!),我常拿这事儿跟姐姐开玩笑并且索要当年她欠我的“债”,她总会笑着回我一句:“乀(ˉεˉ乀)滚!”。也是她读初一还是初二那两年,因为是走读嘛,所以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去,中午在学校休息,所以每天必须带午餐去,有一天她向委屈的跟父亲讲:“爸,我带学校去的饼子中间都是生的……能不能给我两块钱,我中午买几个馍馍吃?”至今有点闹不明白,以父亲的厨艺完全不能做生饼子啊?那当时饼子一定是母亲炕的,这锅必须母亲来背!也不知为啥当时父亲正在气头上?还是姐姐惹着他了?反正就是拒绝了。一向要强的姐姐终究没忍住哭了出来,父亲始终没有心软的扭头做事去了,我当时就在边上目睹这件事情的发生,姐姐哭的很伤心,我不知所措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于是我拿出我的“工资”给了她两块钱。姐姐从小很少见她哭,可一旦被我见到那必须是超级伤心的那种,她把钱拿在手上抱着我哭的更凶了:“好弟弟,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受到她的感染,我也鼻子酸酸的,大概也是哭了吧?其实当时父母亲再穷大概一两块钱还是有的吧?因为平时我都能在父亲那里“赚”到零花钱,我的那几块钱“工资”就是从父亲给的。在河坝树木很多,所以我家一年四季几乎不买煤,可是得天天剁柴火,于是我练就了一副很好砍柴劈柴的本领(那时我就可以做到左手抓柴火右手劈砍的动作,关键是那斧头还贼大,汽车钢板做的那种,不过有一次太得意差点把大拇指砍掉了半截),当时我好勤快的,闲下来没事时我就会去门口的树枝对劈柴,不到俩小时我就能砍两尿素袋再装好背回家去,父亲偶尔见到会特开心,然后大手一挥就是一块钱,也算是对我的鼓励吧!而且我“挣钱”的门路可不止这一样,那时的我咋就那么喜欢卖萌拍马屁呢,哈哈,不符合我的性格呀!为了讨好父亲,我常常给他按摩,按摩脖子,腰,背,腿等部位,按小时计费,比如一个小时五毛钱,我当然没有学过按摩,只是照着电视还是书上学的?按摩指法我是不懂的,反正就是照着父亲的背部掐呀拧呀转圈揉呀,大多数时候是把手掌立起来像剁菜刀剁饺子馅一样在他的身上拍打,这时他总会很享受的趴在那里指挥我需要按哪个部位,有时还嫌我力度不够让我使用脚来操作,站在他的背上来回踩就行。还有就是给他剪指甲,手指甲还好,剪脚指甲那脚气味道一般人真受不了,哈哈,假如有可能父亲读到到这段文字会不会暴跳如雷?毕竟他是非常好面子。一套下来包括剪完搓平收费五角钱,哈哈,也算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吧?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选择“赖账”,十次有两次拿到“全款”就很幸运了,不过我也并非真的要“挣”父亲的钱,马屁(哈哈,新疆话叫溜沟子!!)拍到位让他开心才是最终目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邻居的,在河坝我家原是没有邻居的,之所以称之为邻居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我们两家的关系。在我家东北方向大约五百米的位置有一片树林地,那里住着一李姓人家,有个60多岁的老汉,具体名字无人知晓,外人都叫他李老头。虽然他家的位置离我们村子很近,可户口却是牧业队的。
因为两家相对而言比较近了,所以我们两家也只是处在认识的层面上,路上遇见了彼此打个招呼就了事,基本没有太深厚的交情。李老头家好像有一儿一女,可是很少见到,有没有没有老伴也记不得了,不过传闻说他解放前在河南老家是一个地主,被批斗没法待才来到了新疆过活不知真假。老头性格倔强,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见他外人打交道。印象中他总是一个人独自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平时养鸡种菜活着类似于田园般的惬意生活。
时间再次倒退到1998年或者1999年的春节的大年初一的早晨,那天一大早就听到我家的那只叫斧子的白狗对着鸡圈方向狂吠,一家人都以为是来拜年的客人,连忙开门迎接,一看竟是李老头踏着厚厚的积雪站在后面的地里,父亲见此情景愣了下然后连忙热情的问候新年好然后迎他进屋内喝茶,谁知他却老脸一沉:“你能把欠我的那四十块钱还了!”父亲又是一愣,不知如何答复,这时母亲出门探查情况恰巧听到这话那爆脾气直接开骂:“你明天就要死去麽?大过年的跑来要账?原是我现在没有钱,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那老头虽是年纪大可身子骨却很硬朗,难听话一句接着一句的跟母亲对骂(此处捂头,略表尴尬,怎么把母亲描绘的像个骂街泼妇啊?可那李老头也着实欺人太甚,不懂规矩),骂不过气急败坏了抡起拳头就要打我母亲,可他的拳头还没伸直就被父亲抓在了手里:“你要是来我家做客我欢迎,你要是来要账,对不起,现在没有,就是有也不能今天给你,要账也要看时间!你要是再闹事,别怪我不客气!”那时的父亲体格不是一般的彪悍,用魁梧形容也是可以的。见要不到钱又有可能要挨打的李老头气呼呼的哼的一声扭头走了。即便如此,依旧把父母气的的呀,尤其是母亲,还在那骂骂咧咧的,原本过年该开心的日子被这老头给坏了。后来长大点才明白,原来过年初一到十五的日子是不能够要账的,大概是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吧?就好比做生意早晨没有开张是不能借钱给别人一样的,有种说法是正月要账会让这家人一年都穷,虽然有很大的迷信成分在里面,可总感觉大过年的被人要账确实有点不妥当。李老头那时候已经60多岁的人了,这点道理更不会不懂,之所以敢欺负到我家头上,那就是因为我家摊上一个字:穷!事实上我一直好奇的地方在于当年父母亲怎么会欠他的钱呢?还是买了他家什么东西欠的?总之,这件事发生后过完年父母就上门把钱还给了那老头,从此以后很多年都没在打过交道,好笑的是我跟姐姐从那以后见到这老头也是不在打招呼了,颇有“同仇敌忾”的意思在里面。直到后来上了高中父母和我们才放下这段恩怨,见到这李老汉天天开着三轮车卖土鸡蛋时也会热情的打个招呼,再后来我们家搬到了队上就很少见到他了,也不知还活着没有。
又一次写跑题了,亦不知是第几回了,反正当时的家庭情况就这样,很贫穷很努力也很幸福,回归到之前的主题吧!
在父亲还没来我家之前,脏乱差成了屋子里的特色,用后来父亲的话讲,我家以前所有房子里贴的地板砖(以前农村都拿红砖铺在地面上当做地板砖用)都便黑了,而且还有厚厚的发光的油,那是常年只扫不拖的缘故。每每父亲回忆起第一次来我家做客时情景时总是带着一脸的嫌弃:“那是人住的地方嘛?猪圈一样……”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两个人根本没时间收拾房子,还有就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湖北人真心没法跟青海人比卫生这一块,用父亲的话就是:邋遢……
没办法,父亲只好用铁锹一铲子一铲子把我家红砖地板上“珍藏”了许多年被踩得锃光瓦亮的“宝贝”清除掉了,没钱买拖把就自己造,剪几块破衣服找根木棒一绑,OK,简易的拖把就成了,然后可劲儿的拖,把缺失的部分也找来也趁机补了起来,红砖地板终于再一次可以用肉眼直观的看出来,嗯,那就是一块砖了!除了红砖,顶棚是老早用的那一种宽十公分左右黄色长条类似于薄膜的物件交叉编织的,常年落灰尘在上面早已变得到处是洞洞,睡觉时老鼠从上面经过可以听到明显的响声,父亲把它们通通扒掉,买来集市上最便宜的那种布料四边一订,嘿,还别说真的是整个房间都变得鲜艳起来了呢!
尽管父亲在努力的修葺保养这几间土块房,可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袭,常年风吹日晒加上开春化雪(即便是每年我们都会在三月初及时清理春雪),屋顶的席子(一种用芦苇秸秆编织的长方形农村建房常用的草席,长约三米宽两米厚三到五公分上下)早已腐烂不堪了,每每到了下午变会呈现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场景,于是家里能够接水的工具如水桶啊,盆啊的纷纷会派上用场,谈不上苦不堪言,可这样的场景在外人眼里确实有些尴尬,而且很不体面。
估计是父亲下定决心了吧,跟没跟母亲商量就不清楚了(八成母亲的态度是,随便你,反正我还吼得住),搞,年年上房泥还是效果不好,那就干脆把全部推掉重新盖一个!反正这老房子也是矮了些,盖高点好了,对了,就盖个青海风格的房子吧!
在原有的地基上,父亲把前面的那一面墙用红砖砌的,后面依旧选用拆下来的土块,当时应该没有余钱买红砖吧?从没有做过土建的父亲凭之前看别人做而模仿着一瓦刀一口灰或者一口泥的把砖,土块砌成了墙。梁,檩条都是选用河坝现成的扒了树皮晒干的杨树,与之前的房子不同的是这次建筑有了更大坡度,很利于排水。而且檩条伸出屋檐一米左右,从远处看去更像是人脑袋上带着个大檐帽。最与众不同的是檩条上并没有直接铺设草席,而是在檩条上铺满了用被劈开的木棍(长约三十公分,间距十公分,就是平时烧火做饭用的柴火)整齐的摆在上面,用父亲的话讲这才是青海风格建筑的特色,他自豪的说:“在我们老家呀,这么铺上去,房顶上开个小手扶上去都压不塌!”在那一排排小木棍上面铺上草席,再盖一层蓝色的塑料布最后上一层十多公分的土就算大功告成了!
为了屋内不再像从前那么的阴暗,父母买来了两副大铁窗(长2米,高1.5米左右),两副小铁窗(长1.5米,高1.5米),也是整个翻新旧舍投入资金最多的一项开支吧?砌墙时拉线,用水管加水定水平,砌柱子时拿半截红砖绑根绳子提溜在前面闭上一只眼看垂直度,安装窗户和门时会在上面搭一根长木棍,然后绑两块红砖压住它们再调整垂直度和水平……这些都是我看着父亲做的,往后很多年我问过父亲他到底做没做过土建工程,他总是不正经的回答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麽?我是来新疆以后自学成才的,哼,别小看你老爸半吊子水平,雇个大工不一定有我砌出来的好哩!”说这话时眉宇间带着藏不住的自豪,那是属于他的吹牛的资本,在我看来看来一点也没夸大,所以通常我都会一脸膜拜的配合他:“那必须的,必须的!”。
对了,盖房期间除了母亲偶尔给他打下手外还有一个青海老乡在我家暂住,姓甚名谁已记不得了,包括父亲应该也记不得了吧?青海人四海皆兄弟,初来陌生地域只要有老乡就会去投奔,主人家也绝无嫌弃之意,当然,他们也从不白吃白喝,就当自己家一样尽心尽力的帮衬主人家做事。只记得他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每到晚饭过后跟父亲饮两杯小酒,然后趁着凉快的夜色拿出他随身携带的二胡来为我们一家人拉上一曲,偶尔父亲会陪着吹他的笛子或者跟着二胡的节奏唱起来青海花儿。我从小不懂音乐,仿佛血缘里压根没有音乐细胞所以听不出是否专业,可记忆里的二胡声是那么的好听,若是没记错的话当时他还演奏过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呢!别看他年纪大了,可力气却丝毫不比年轻人弱,上房梁时那几颗杨木有成年人腰那么粗四五米长,他跟父亲一前一后硬是把它们安装上去了,先合力把一头举到其中一年墙上,另一头一个人拿根粗绳子站在墙上往上拉另一个人抗在肩上往上举,那是建房最为困难的工序,既需要力气和技巧还要求两人有默契的配合,往往这时母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俩总会让母亲和我还有姐姐站远些,怕出什么闪失。还有就是这个大伯饭量也是惊人的,往后多年的父亲偶尔回忆起这位老乡总是带着夸张的表情说到:“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一口气干掉七八个鹅蛋的人,能把鹅蛋当饭吃,厉害……”,是的,当时我家虽然很穷,鸡鸭鹅肉是从不缺的,而且那一年家中正好在养鹅(往后就这这段日子),缸里腌了大半缸的头照蛋,所以有段时光餐桌上顿顿有鹅蛋的出现。因为这大伯做事不吝啬,我家在饮食上更不会小气,隔两天就杀只鸡宰只鹅的,他呢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吃半只鸡鹅再加两三个大馒头估计都是为了给我家人留点菜的意思。
就这样主要是他俩盖,母亲偶尔帮忙,我偶尔放学给他们端茶倒水递个砖啥的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样子,一个面积约有 90平米的六间土房子就基本上快完工了!最为难忘的一幕是在上完主梁时父母还走了一程仪式,那天他们破天荒的去街上买了一挂五千响的炮仗,买了糖果,葡萄干,红枣,饼干等加起来约两三公斤。最让我我觉得有趣的是,父亲让母亲找来了一块红布,又问母亲要了几块她收藏的钱币(好像有几块银质的首饰?对了,好像是母亲的一对耳环!),它们包裹在客厅下方的那个主梁上,又用了两三枚一分还是两分钱硬币当做钉子钉在了那颗杨木上。找根长棍挂上炮仗,随着鞭炮声响起,父亲站在墙上开心像个孩子从塑料袋中大把的抓起里面的零食往下丢,观众当然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外加一个青海大伯,受到情绪感染,我们跟姐姐也像只爱凑热闹的小鹿飞奔过去抢糖吃,大伯也极力配合到各个屋子的角落去捡着吃,只有母亲一脸笑吟吟的捉着菜刀在切肉,然后没忍住:“木子啊,给我拿一颗尝一下嘛!”
就这样,我家的从此告别了阴暗低矮的土块房,走进明亮高大的……好吧还是土块房,面积还是那么大,可给人的感觉是空间仿佛更大了,而且也没那么压抑了。这房子我们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2016年秋天我家搬到村子盖的抗震房后它才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直到2020年五月20号,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庇护我前半生另一半时光的那几间青海风格的土块房彻底的消失了,因为我家的老房子在河坝附近,那一块属于湿地保护区,政府统一拆迁并且给在镇上分配了一间近100平米的楼房。
老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它见证了我们一家拼搏向上积极奋斗的历史,好在留下了不少影像资料,偶尔怀念便看一看也就释然了。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749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