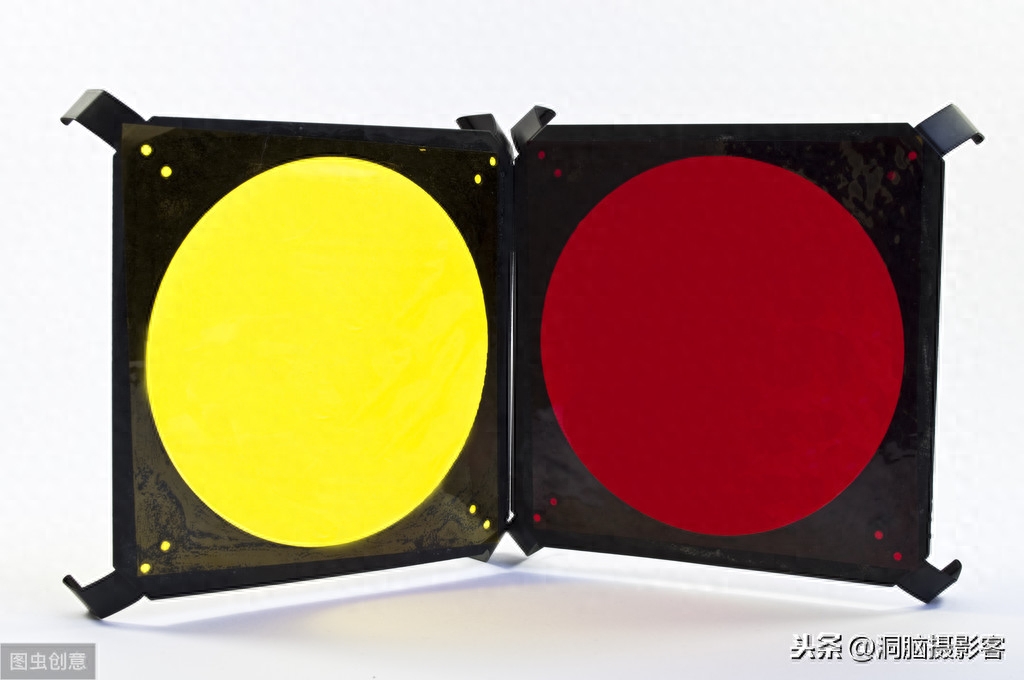愿像野菊花那样美丽,倔强而又野蛮生长
文:梅子

多病的童年
我总是在想,我也许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可是,我还是幸运地来到这个世界。
我小时候,一直感冒生病。一发起烧来,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每次,一到半夜,我高烧发起,母亲抱着我,大声叫着:筷子。姐姐从睡梦中惊醒,她爬上小凳子,从筷笼里取出筷子,递给母亲。母亲把它们硬塞入我口中。
邻居王大伯,一边穿衣,一边拿着手电筒,匆匆往外赶。他去找赤脚医生。我不知吃过多少安乃近。圆圆的,大大的一粒。最小的时候,母亲用做菜的刀,把它切碎,化在碗里。再后来,母亲分成四半,叫我吞下。
安乃近,偌大。我拿起一瓣。放在嘴里,水咽下,药却停在喉边。苦味,化开来,一下浸润了每个细胞。我身上便泡满了苦味。
我的手上扎满了一个个针眼,旧的未褪去,新的又来了:青带紫,紫透红,红嵌黄。
每次一发病,我都会住院。大年三十,别人在家张灯结彩,欢笑不已。我们一家在医院里。
我躺在医院里,一睁开眼:米白色的墙,恍恍惚惚;昏黄色的灯,在我眼前摇曳晃荡;走廊里传来隐隐约约说话的声音。随着一声“醒了”,那好看的医生俯下来,量着体温:总算退下来了。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逃过了一劫又一劫。
在那些个晚上,我一不留意,就过去了。我是那个邻居口里的“金桔饼”。奇怪的是,上了小学后, 我再也不生病了。

窘困的家底
我家一开始挺穷。穷得只剩下一座木房子,一张古床,一个介橱,再没大的物件。最值钱的是那张古床。床有床帘,四周包围起来。两侧雕刻着精细图案,每一幅宛似一个故事。我总是喜欢站在前面,摸着一道道刻痕。
可是,我的爷爷很富,是地主,我们的这排屋子,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曾是爷爷的房子。可惜,他把它们都卖了,自己带了小儿子,新老婆,走了。从此,父亲和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祖母死后,只剩下父亲:一座小木房,一个人。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缸里只剩下一勺米。所以,父亲母亲拼着命儿支起家。他们做过甚苦的砖窑工。我去送饭,见过他们:母亲在前头,单车的前头系上一根麻花粗绳,她紧紧攥着粗绳索使出全身力气,往前拽。
父亲在后面架起单轮车,母亲在前面拉,一辆摇摇晃晃的单轮车,跌跌撞撞地向前驶去。遇到上坡路时,父亲紧绷着脸,两脚摆开,左脚略微朝前,然后竭尽全力,拼命朝前冲去。
可是坡陡 ,拼命使劲,单车却一动不动,再使劲,非但不动,而且顺着坡势直往下掉。径直退到地势平坦之处,单车轮子才嘎然而止 。
父亲停下来,歇下单车,母亲急步走过来,递过水壶。父亲大口大口喝着水。喝完水,父亲用手背擦擦口角,又拉起单车。
我看着父亲母亲,连忙跑上去。

愿像野菊花那样美丽,倔强而又野蛮生长
我喜欢爬上山坡,坐在那大石头上,数着对面那一座座山峰,一共十八座。
我也喜欢听大人们的传说,在那十八座山峰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太监有宝藏,传说,一对私奔的情人来这儿殉情,女的跳下了,男的害怕了,没跳……
每当这时,我的遐思翻过一个弯又一个弯,仿佛连绵不断的山峰。
在那村子的另一边,是一簇簇的矮丘。一个个坟,齐齐列在那儿。我害怕,去那儿,总害怕那儿钻出鬼魅。
有时,我也和小伙伴唱着歌,赶着羊去那儿。春天的时候,那儿开满了晶莹的梨花,一片片,和着绵柔的春雨,酥软了心。我最喜欢那野菊花。每到秋天的季节,满地的野菊花爬满了山坡。就开在就开在山坡上,沿崖边,就开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簇簇,一丛丛,枝枝桠桠,迎着风,盈着笑。花瓣儿堆集着,细细密密,合拢着,簇拥着,缠绵在一起。它们悄悄探寻着,打量着,小心翼翼绽放……
每一朵,都是怒放的生命。
我总是在想,当一朵野菊花,挺好的,那么傲娇,那样野蛮疯长。也许,我当不了花,那像稗草一样,也挺好。
在家乡田里,总长满了一株株稗草。不管怎么风吹雨打,一次次被拔起。过几日,再去看,永远有零零星星的稗草,横亘在那儿。
嫌弃也罢,讨厌也罢,它还是在那儿,等到稻熟了那天,它也熟了,结着沉甸甸的穗子。
我总是讨厌着它,却也莫名喜欢着它。

压力下的动力终是有一天会被反噬
小时候,我没特意好好读过书,但我们姐妹成绩却很好。我们一边干着农活,一边读着书。我不想上高中,我想上中专。可是那一年,我却考上了县里最好高中。
我坐在灶前,用火钳往灶堂塞着柴火。火熊熊燃烧着,映红了我的脸。父亲不苛眼笑的人却舒展了脸,母亲也微笑着。没人能明白我的心思。
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是不同的。这份不同是从我踏进高中的大门后那一刻才深深被感知。那份刻在骨子里,深深的,自带的自卑,如影随行。
是的,自卑。就像多年以后,他所说的:回答个问题,老师目光一扫,恨不得把头埋到桌子底下去。
我也自卑,或许更多承载的是那份压力。因为我们的一切,是父母的血汗叠加而成,我们必须好好读书。
我没考好。压力胁裹下的动力终是有一天会被反噬。我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家里的一切:旧的门板,旧的窗棂,一如既往地立在那儿。
邻居家的大伯阿婶们在那门口,高声谈着谁家的孩子上了重点,眉飞色舞讲着。远处屋檐下零零落落悬落着的蛛网,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爬着吐丝。
突然,一种莫名的疼划破了我心房,我深刻明白那种无奈悲哀。
父亲闷声不响地坐在小凳子上,妹妹立在旁边一动也不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悄无声寂的窒息,浓浓密密,压得人快喘不过气来。母亲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重重地叹了口气。
好久好久,父亲拿起镰刀,轻声说:“走吧,去地里吧。”

我的大学,我的奋斗
我上了一所并不是心目所愿的学校。大学里,我和室友去卖过报纸。后来,我去做家教。那是一个四川的布商。在那一年暑假,她女儿进步很大。她连给我介绍了三家家教。
她对我说:我很敬佩你,当然,若你教得不好,我也不会给你介绍。
所以,整个暑假,我都在做家教,早上一份,中午一份,晚上一份,每次三个小时。小学十元一个小时,初中十五元一个小时。夏天,我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炙人的热浪,泡得让人晕过去,或喘不过气来,胸中沉沉压抑着。是的,我心脏似乎不好。会心慌,会气闷。
开学了,我还是继续着家教。在风起的时候,在雷鸣不止的时候,在雪暴下的时候,我一个人孑孓而行。我站在公交车上,车子摇摇晃晃,我也跟着晃晃荡荡。外面飘着鹅毛大雪……
当我熬不下去时,我会想起我的父亲母亲:
在那集市里,手忙脚乱打秤的,却还是被人顺手牵羊偷走葡萄的父亲;在那暴雨如注时,他慌乱地赶着往外游走的鱼儿,那是他已养了一年肥了的鱼;在那稻田里,赤着身,晒得滚烫赤红他的脊背。还有,被那打稻机压得直不起的腰。
我想念姐姐,也想念妹妹。我总喜欢看那灯火下,一潺一潺的跳跃的小脸。母亲一针一针织着秋凉的毛衣,有时,她也转过头来,微笑地看着我们。
当她们满意地把工资递给我,我又激动又小心翼翼地数着钱。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我用自己做家教的钱养活了自己。我把余下的一万二的钱交给了母亲。
那一年,我们二十三岁,大学室友涂着亮丽的口红,擦着美美化妆品,吃着精美点心,身倚靠着一米八的男友。

我只是想抱抱曾经野蛮生长的自己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希望我回家乡工作。他拉着我去见一个人。那人翘着二郎腿,喝着茶。他斜着眼,看着我们。又看了看,那一袋袋东西。那是父亲准备好的农家土特产。
那人眯着眼,坐在那儿,不理我们。父亲和我立在那儿。他很窘,两只脚在那儿。有一只鞋子,沾着一块褐色泥巴,那是早晨父亲采摘葡萄,不小心沾上的。他伫在那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是我的父亲,一辈子卧在土地里勤勤垦垦的父亲,他不曾向谁低过头。
回来后,我流泪了。我对父亲说:爸,你不要再去找他了。我在外面很好。我想躲得远远的。近了,我怕他们知道我过得不好。我怕看到他们担忧牵挂而又无助的眼神。

我再次拿起行囊,远离了我的故乡。独自一个人,背井离乡。后来,我受到了老板的器重,再后来,我遇到了老公,嫁人,生子。
许许多年以后,我再回过头,去回忆。
那个一直在路上颤颤巍巍的女孩,一个瘦小,单簿,孤单的身影:那个一直想当老师,想当记者,而一次次擦肩而过的女孩。
有时,是会有那么一丝疑憾,有一点失意,但一点也不曾后悔。她的人生,每一次,都曾用力活过;
是的,我只是心疼她。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1921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