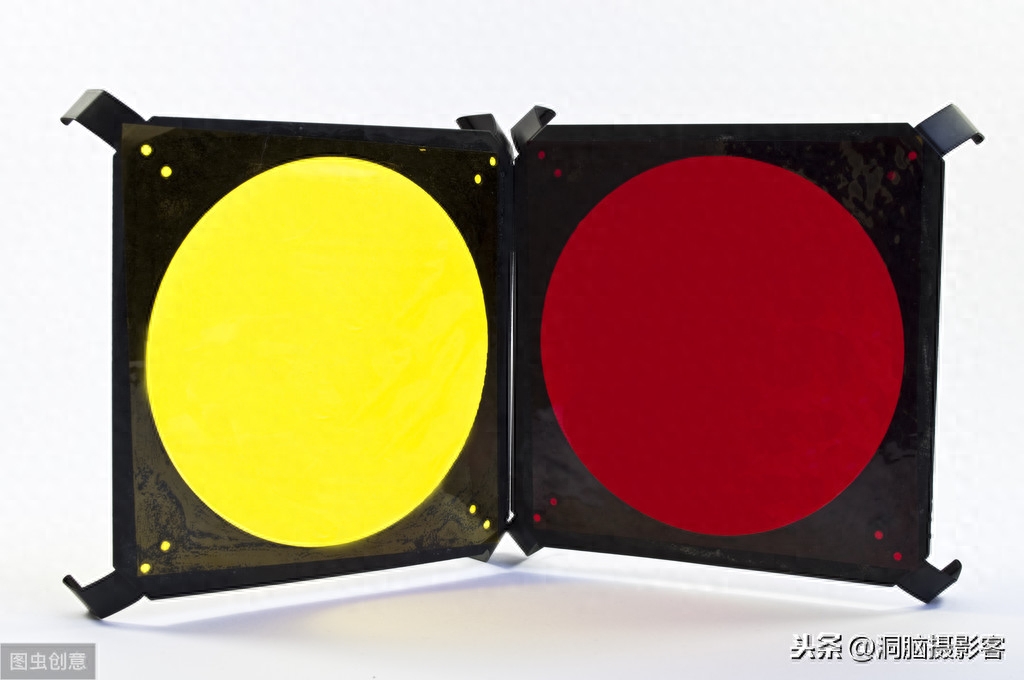为了替自己在人生中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我竟舍弃了奶奶

寒天情思
冬天的风真吓人,连那淡淡的冬日似乎也对它无可奈何。寒风夹着雪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的声响,连时间都好像被这凛冽的寒气冻住了,美容厅门口那只大钟的指针每移一小格,都得捱上老半天。
虽说我在美容厅挣外快有一个多月了,可我的眼睛依然无法习惯于修指甲这份差事,还未下班,眼睛好像已支撑不住了。
因为临近圣诞节,虽说气候奇冷,美容厅里还是生意兴隆。我已记不清这回搁在我膝上小瓷缸里的是第几双手了。不过这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修剪过的那双双白嫩细润、如象牙细雕出来一样的典雅高贵的手,而是一双老人的手。在白开司米袖口衬托下,它清瘦松弛,满是皱纹。对我来说,这样的手十分熟悉,它和我已故去的奶奶的手,还有那位慈祥可亲的海杰太太的手是那样相似。我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扑向这双手。手的主人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她戴着早在六十年代流行过的那种蝴蝶式角边眼镜,红褐色的衣领也是老式的,且已陈旧了。她不像那种随意挥霍的爱时髦的阔太太,可是对自己这双手却是如此钟爱和讲究。其实,既然这不过是一双不时颤抖的老妇的手,实在犯不着冒着寒风上美容厅来这样花费一番。
“可爱的蓓蒂今晚歇班吗?怎不见她?”老妇浑浊的双眼四下顾盼着问,带着浓厚的爱尔兰口音。
“哦,她去洛杉矶了,准备明年暑假进大学。”我不经心地回答,没有告诉她,我顶的就是蓓蒂的缺。
“这么说,她走了!”老妇遗憾地叹了口气,“再没人比她修指甲修得更好了。”
我撇撇嘴没吭声;心想这老妇虽说年纪那么一把,在修饰上倒一点不肯马虎。怪不得妈至今都看不惯白种女人,妈说世界上最正派的还是我们中国女人。这话说的有理。拿海杰太太说,虽说嫁了个美国人,却向来不见她涂脂粉。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成天价穿那件白开司米衫和深色旗袍。那时我是不敢正眼看她的,既然她是我的东家,用咱们道道地地的中国话说,那就是“衣食父母”呢。再说,我向来怕看老人的脸(奶奶的例外),那干瘪得像核桃的脸面瞧着真不舒服。因此当时我目光所及的,就是那双衬着白开司米衣袖的手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差事——陪伴老人,这有多乏味!我们班上随便哪个女孩子的额外差事都比我好,特别是那漂亮的金发碧眼的琪恩,她凭着一头金发和丰满的身材,就在一家快餐厅里帮忙售汉堡包,惹得男孩子们都往她柜台前挤,可神气了。不料妈听了却直吐舌头,她说要她是琪恩的妈,宁可供她零花钱,也绝不让她去卖汉堡包。可我,不说凭着又瘦又小的身影别想找到这样的差事,餐厅里洗盘子都嫌我小。都十七了,还花爹妈供的零花钱,这不丢人吗?所以我也就硬硬头皮认下这份乏味的陪老人的差事了,好歹每小时也有三美元。
“过来,孩子!”那次,海杰太太向我张开双手招呼道。那双手一直在微微抖动着,就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抖动,才使我的厌恶之情转为怜悯。我迎了上去:
“我们这就去花园散步吗?太太?”
“别叫我太太,按我们中国习惯,叫我奶奶吧,好吗?”她双眼流露出那样一种高兴满意之情,这使那张核桃一样的脸显得十分慈祥和容易接近。
可是我没吭声。我有自己的奶奶,她是我深藏在心底的亲人,谁也不能取代她。
“我的奶奶死了,上帝把她召去了。我再也不会有奶奶了。”尽管当时奶奶已离开我近半年了,可一提起奶奶,我还是想流泪,或许因为我是从小牵着她的衣角长大的缘故吧。
“哦,你奶奶是幸福的。尽管离乡背井几十年,好歹还是在中国式的家庭里度过了余生。”海杰太太听我介绍了奶奶的一生,微微怔了一下,然后说。随后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搭着我肩膀向花园走去。
海杰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在关岛,因此海杰太太就全靠那份养老金过活。不论是那边缘已经十分残旧的地毯,还是那一夸脱[20]一夸脱零买的咖啡豆,都说明这份养老金是很微薄的。然而她却有一个收拾得很精心的花园。起先我很诧异她怎么会有如此精力,后来我才知道,每两星期即有一中年汉子来帮她收拾花园,另外还有一位太太每星期来两次帮她整理屋子。想象得出,这个花匠和钟点女佣将花费掉她很可观的一笔。我奇怪老人竟是这样不会安排,不会计划。
就像每个星宿都有自个的位置,海杰太太也有她的位置,那就是起居室近窗那把高背沙发。她常常坐在那儿,久久地凝视着壁炉架上海杰先生的遗像,或者一只旧花瓶,一把椅套已褪色的安乐椅,然后唠唠叨叨地叙述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起初听起来很新鲜,可听多了我也厌了,犹如听一张反复播放的陈旧唱片。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并没将什么新的曲调录入她的记忆里。
“讲点什么吧,孩子。当初蓓蒂总对我讲点什么。我老了,替我修指甲不用怎么讲究,只消对我讲点什么……”爱尔兰口音的顾客对我说。
这是那样满怀热望而又怯怯的惟恐对方嫌弃的请求,而且同时她的手还微微一缩,好像准备随时抽回去似的。那近乎哀求的语气与海杰太太的竟是如此相像。
当初海杰太太也是这样。每逢花匠和钟点女佣来的日子,她才间或离开她的位置,拄着拐杖跟在他们后面,轻轻地惟恐对方拒绝似的恳求着:“讲点什么吧,我老了。替我做事马虎点没关系,反正没有人来做客……只消对我讲点什么……”也只有这时,她才拿出那套银制咖啡具(她的结婚纪念品)。当壶里冒出香喷喷的咖啡香,她便吩咐我,配上一小碟可口的干点招待他们。花匠或女工啜饮着可口的咖啡,与她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咖啡完了,他们也走了,留下一堆渐渐凉下来的咖啡具……人们够忙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一个老太婆啰唆,况且他们的分内事已做完了。于是海杰太太迈着蹒跚的步子,又回到自个的位置上去。我算懂了,她是多么需要与人沟通,她宁可从微薄的收入里抽出那么可观的一笔,只是为了逃避孤独与被人遗忘……就是眼前这位带爱尔兰口音的老妇人,冒着严冬厉风,来到美容厅,想来也是为着这……
“您让我想起另一位太太,她跟您很相像,虽则她和我一样是中国人……”我不禁停下手里的活,向她叙述起海杰太太,我明白这对于她远比修指甲重要……
那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不能出去散步了,只能待在昏暗的起居室里。房里没有开灯,海杰太太耽于暗淡的程度犹如我习惯于追求光亮一样强烈。雨拍打着玻璃窗的嘀嗒声和风吹动树叶的簌簌声,使我感到说不出的凄凉和悲哀。我想起了奶奶,她就是在这样一个雨夜离开了我们。她的魂魄究竟在哪?会飞回她老家,她那念念不忘的中国浙江那个小村吗?听奶奶说,家乡祖屋前有一棵洋槐树,当风吹过时,它也会发出这样的簌簌声。
“你哭了,孩子。”海杰太太说。
“大约是的,我忽然想起了奶奶。”
“我也在想我的奶奶……”
她的奶奶?那似乎是十分遥远的了。
“这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时我才九岁,第二天就要随父母漂洋过海了。我到奶奶床前去向她告别,她眼里滚动着一滴泪珠,我用手指抹掉它,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离别的滋味……又苦又涩的离别……”
我默默瞧着海杰太太一头稀疏的白发,想象着她九岁时的模样,可是想象不出。
“那阵我可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头发,也会变得像奶奶那样灰白……看我讲到哪儿了?对,我们一直很惦着奶奶,可心疼钱,竟再也没回去探望过她。后来待我们有能力了,她却已离去了……我们老家四周都栽满了桑树,风吹过时也是这样簌簌作响……”
呵,我们竟想到一块了。看来不论是十七岁还是七十岁,心灵有时是能相通的。这时海杰太太猛然起身,不用拐杖就走到和她同年的钢琴前,一双苍老的青筋绽起的手按在琴键上,先是微微一缩,后又缓缓舒开,这令我想起含羞草,可在她按出第一个音阶后,那双手即刻显得那样轻巧柔和,那深情忧伤的旋律令我听出是舒伯特的《菩提树》:
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我的双眼,
好像听到那树叶在对我轻声呼唤:
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
她双手无限柔情地抚弄着琴键:“我女儿最爱这首曲子……”我想,当初她拍打着襁褓中的女儿时,一定也是这样温柔的。钢琴上相架里那位漂亮太太也瞪着双目在沉思,她就是海杰太太的女儿,在西部安家谋生。她似乎很忙,难得有信,而且经常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在她听到风吹动树叶的簌簌声时,她会想到自家门口那棵菩提树吗?她会想到孤苦寂寞的老母亲吗?我两手托腮,不觉已泪流满面,第一次深刻地感到人生的无可奈何。
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海杰太太那安详自得之情一下扫光似的,她疲乏地起身走向她的老位置,疲惫不堪地往沙发背上一仰。那双白里透青,连指甲都晦涩得失去光泽的手,十分疲倦地搁在沙发扶手上,它们有过青春,有过欢乐,曾经充满生机,然而……
“海杰太太,你应当写信让你女儿来看看你,她有这个能力……”
海杰太太缓缓地摇摇头:“每人在生活中总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上帝安排的。我女儿一直不来看我,自有她的苦衷、她的为难之处,就像当年我对我的奶奶一样……”
此时,我算真正悟到我肩上的担子了。它要承担的不仅有海杰太太那双衰老无力的手,而且还有她那颗孤寂无告的心哪!
这种感觉在那年耶诞之夜更为深切。本来那晚琪恩已邀我去她家过节了,这既可解一解我节日的寂寞,又可给我一个展示那件大红天鹅绒裙子的场合。可是傍晚,当空气中弥漫着“平安之夜”的乐声时,当远近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飘出叮叮咚咚的教堂钟声时,我想起海杰太太。当然我有一千个理由自由享受佳节之乐,可是……她有什么欢乐呢?除了女儿寄来的一张“妈妈我想念你”的圣诞卡片,还有什么呢?难道我忍心看着她孤零零地在她的位置上挨过这节日吗?
当我在海杰太太台阶上跺掉鞋上的雪时,我即刻听见她喜出望外的声音:“是你吗?小宝贝!”那晚虽说我们没有圣诞火鸡,也没有人赞扬我的红天鹅绒裙子,可我过得很快乐。耶诞奇妙安宁的气氛像巨浪一样笼罩着我,我曾经为一颗孤苦的心带来瞬间的欢乐和光明。
“可你最后还是离开她了?”那位带爱尔兰口音的太太说。
是的,或许是我太自私了。可是……上帝饶恕我,我是个女孩子,快满十八了,世界对我的吸引力有多大啊,恰巧这时我有了进美容厅挣外快的机会。且不说那里的报酬远远超过海杰太太所能支付的,光那些进进出出的女主顾们就足以吸引我。在那里我能见到在我们唐人街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的上等场面。连骄傲的碧姬都不胜羡慕地央求我:“千万替我留神一下路易十六式的发髻该怎么梳……”我必须舍弃海杰太太。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无可奈何和严酷。海杰太太的态度完全出乎意料,她冷静地挥挥手说:“去吧,孩子。老守在我身边,你会变成一朵由人践踏的小花的。应当出去闯闯,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位置。我不难为你。人生嘛,儿童的乐园,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她的话令我不敢正视她的脸,我只盯着她那双紧抓着沙发扶手的手:薄薄的皮肤似乎马上要绷裂,就跟我奶奶临终时抓着床沿的挣扎一样。奶奶!我很想扑过去这样称呼她,可终于克制住了,我怕这样做反而增添离别的忧伤。就这样我离开了她,为了适应即将面临的艰难的人生,为了替自己在人生中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我竟舍弃了她。
“……在你去探望海杰太太时,别忘了替我问候她。”那带爱尔兰口音的老妇临走时这样对我说,同时把一美元小费塞在我手心里。我像让火烙了一下似的缩回了手掌:难道什么都得用金钱购买,即若人与人之间那么一点交往和关心,也离不开金钱吗?我小心地替她披上那件薄薄的看来是抵不住这凛冽寒气的大衣:“留下您的地址,您以后遇上这样坏天气,用不着出来,我可以上您家。”老妇在我颊上吻了一下,那耶诞之夜曾十分感动过我的巨浪又一次涌上我心头。
我实在应该去看望一下海杰太太,我还一次也没去看过,虽说我已下了一百次决心,可是,每天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第一个休息日我参加了郊游,第二个休息日……我把钱花光了,买了套苏格兰呢裙子,没钱怎能去做客呢……上个休息日……贝茜的车没空,通常总是她载我一段路的,不过今天下班后,我却无论如何得去一次。
真巧,下班后风倒停了。覆满白雪的路宛如一条洁白的带子。脚下雪嘎吱作响,寒气刺鼻,远远地我已看见海杰太太那幢小屋和门口的菩提树了。我小心地护着手里那束玫瑰,想象得出海杰太太看见了会有多么高兴。这回呀,用不着她说:“讲点什么”,我就会滔滔不绝地倒给她一大堆新闻,还有那位带爱尔兰口音的老妇的问候。我在台阶上用力跺跺双脚,留神着“是你吗?小宝贝”的声音,然而没有,四周是一片不祥的寂静,连菩提树的稀疏的叶子也在严冬的宁静中屏息着,一动也不动。这时我才发现门口挂着一块“出售”的牌子,署名是她的女儿,出售原因是“屋主亡故”。为了证实我没看错,我还伸手触摸了一下那块牌子。那一阵冰冷,瞬间把我的心都凝住了。一阵深沉的痛苦扼住了我,我已犯了一个永远难以挽回的过失。
“对不起,亲爱的……奶奶!”
一片雪花打在花瓣上,即刻融化了,永远消逝了,我把花搁在她门口那难得有信件的信箱上。
我默默踏上归途,嘴里反复念叨着那位爱尔兰口音老妇的住址。谢谢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时看来脆弱如雪花,但还是可以弥补的。只是时间可不容许你耽搁、拖延!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2236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