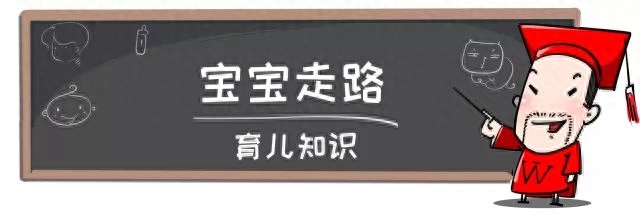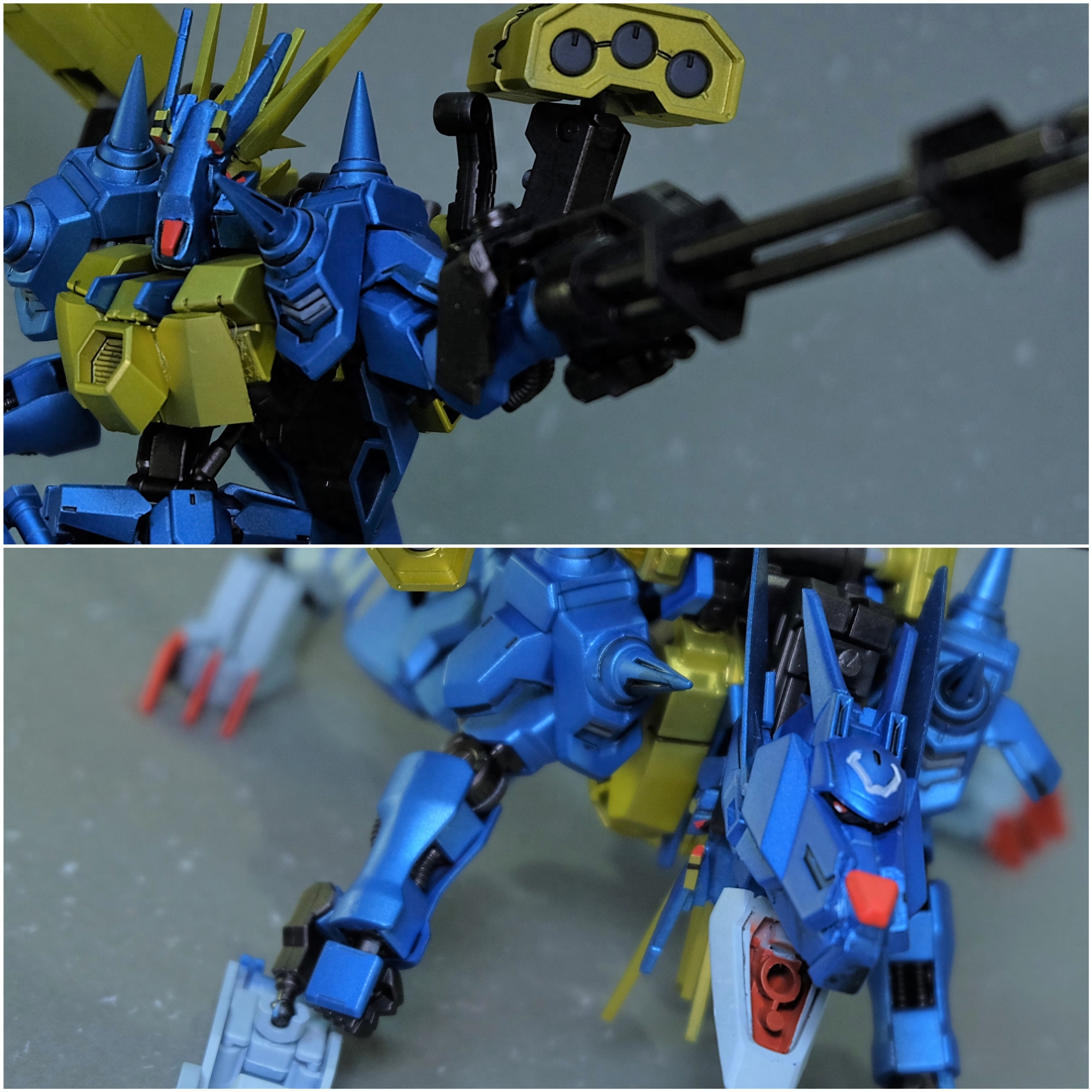世上曾有张博伦
一
写写张博伦是很早以前的想法,一耽搁就是二十年。
四十年前,有人向我说起过张博伦,那时他大概四十来岁。我最初听见这个名字,直觉是咋起了一个英国首相的名字?尽管,后来知道英国首相张伯伦是伯仲的伯。另一想,如果他的父亲有留学西方的背景,望子成龙,期待他成为中国的张伯伦,也未可知。
2019年6月24日晚,张博伦当年的工友、琴友们赵玉福、李同新、胡国华、毕玉奇等一起坐在了众品食府,回忆曾经在一起吹拉弹唱的好时光,透露张博伦的父亲张香严,原籍济阳,真的在西方留过学,先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采矿专业,后游学于德国,张博伦曾让赵玉福看过父亲收藏的德文书,关于摄影的,扉页上有他父亲的德文签名。学成后的张香严先在青岛落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授,又在博山华东煤矿任工程师,是经理朱凯之的左右手。张香严虽求学日本,却对日本觊觎中国资源恨之入骨,精通日语回国以后从来一句也不说。1938年,张香严夫妇动员弟弟张最时悄悄参加了革命,后为某野战军第五十军司令员。小时候的张博爱清晰地记得父亲与外商在家里谈判煤炭交易,从早上谈到晚上,全部英语。1948年,张香严去济南公干途中死于战争炮火,去世时才三十八九岁。

前排:张博伦母亲、外甥,后排右起:张博爱、张博伦、姐姐、哥哥
母亲金鞠平出身农家,却禀赋聪颖,过目不忘,在丈夫影响下读书看报,喜欢向左邻右居舍读私塾出身的乡贤请教,极富修养,《红楼梦》里的诗词过目成诵,曾出任多年新村村委会妇女主任,谁家打仗,都找她调解。自然灾害期间,宁让自己的六七个孩子饿肚子,把省下来的菜窝窝接济了更没啥吃的人家。中年丧夫,金鞠平一人带着六个孩子,旧衣服大的穿了二的穿,冬天穿了掏出棉花夏天穿,一个个把他们拉扯大。
说话间,张博伦离开人世已近二十余年。知道有今天这个会面,当年张博伦过从甚密的琴友之一李同新十分激动,事先写好九页纸的提纲《生不逢时空有鸿鹄志,命运多舛折翼凄凉归》,供我采访参考,果然十分受用。
二

张博伦
张博伦,1942年出生,有幸考进淄博一中,时任音乐教师王鸣公开号称两大得意门生,一是吴雁泽,一是张博伦。在王鸣门下,吴雁泽主攻声乐,而张博伦主攻作曲。他与王鸣老师都参加了在杏花天的大炼钢铁,抡锤子砸矿石,师徒两人相约,砸不完矿石就不剪头、不剃须,整日蓬头垢面。1959年,吴雁泽如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代男高音歌唱家,更加激发了张博伦考取中央音乐学院的愿望。1960年,他郑重地填写自己的志愿,第一志愿:中央音乐学院。第二志愿:中央音乐学院。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赌气,他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挑战冥冥之中的乖气,如果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不能一步登天,那就把自己狠狠摔在泥里!他用捏笔捏得出汗的手,写下了他的第三志愿:广北农校。广北农校是山东省广饶县广北农场下辖的一个农业技校。广北农校在惠民专区广饶县,1958年10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通知,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区,故广北农校在淄博招生。
命运第一次向他露出狰狞。张博伦徒有远大理想,录取他的却是广北农校。
有人说,他失去中央音乐学院的青睐,是因为出身问题,有一个留学西方的父亲,还有一个名门之后的母亲,那个唯出身论、唯成分论的年代,你就是插着翅膀也休想起飞。也有人说,曾经看过他们家的户口本,出身一栏是空白,不该是因为这一问题。那种极其敏感的年代,出身空白本身或许就是更大的问题。还有人说,张博伦落选中央音乐学院是因为中耳炎所致,而他报考的作曲专业,对听力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面试的时候一路顺利,在视唱练耳环节,他功亏一篑了。当时,他的志愿是报考器乐演奏,王鸣老师认为他的理论作曲比吹笛子好,让他报考理论作曲专业。无数朋友为张博伦惋惜,你就不该报作曲专业,若是报器乐,吹个笛子,绝对是高手。可惜,一切扼腕都是多余了,他打上行囊,从千年手工业繁荣之地走向了广袤荒凉的黄河滩涂。
广北农校如获至宝。张博伦的到来,甚至改变了广北农校的文化板块,他既会吹拉弹唱,又能作曲,立马被拉进学生会,不久又成为广饶县人大代表。如果广北农校不停办,张博伦也许可以演绎一个身陷逆境、终成卓越的励志故事。但命运对他就是如此残酷。 1961年1月,山东撤消淄博专区,复置惠民专区,专区机关由淄博迁回滨县北镇,学校停办解散,黄河入海口不再收留这个山城子弟。他精神恍惚地回到了博山,重新就业,去了博山美术琉璃厂。他的艺术之梦还一息尚存。美琉聚集着一批内画艺人,干不成音乐,能够拿起画笔,也能寄托内心的灵秀之处。分配工作的时候到了,他与内画无缘,他的岗位在大炉,需要他冒着上千度的高温辐射去拔条,去吹制琉璃器皿。他再一次使出了骨子里头的执拗,不能画内画,就去最苦最累一身汗一身泥的基建工地当小工,搬砖头扛水泥搋泥窝。这是一个驴脾气的人,遇到逆境便走极端。不会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也不会低三下四服软求人,他后来常跟琴友李同新说:“情愿走这滩泥窝,也不走那堆炉灰。”走归走,情愿二字是真的才怪,只是他骨子里始终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文人气。

张博伦与母亲、姐姐和外甥合影
三
1964年,周村的淄博无线电六厂从美琉调人,张博伦再次看作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很麻利地报了名,再一次离开博山,没有一点障碍。厂领导很喜欢音乐,无奈曲高和寡,张博伦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张博伦却陷入再一次沮丧,工厂就是个音乐沙漠,除了厂长喜欢音乐,工人当中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谈论曲子的工友,如果不离开这个地方,假以时日,张博伦非把自己逼成一个哑巴不可。
厂长慌了,到手的音乐人才必须留住。谈心,给张博伦买上各种乐器送到宿舍,让他独享,并承诺他尽管玩乐器,可以不干活,只是不要调走。张博伦的二姐张博学时在周村广播站干播音员,姐夫是航校教官,这两位曾经被厂长请来当说客,没有成功。厂长看看他的架势,这头驴不是一般倔,只好做了顺水人情,放张博伦回家。
张博伦回到博山,区劳动局把他安排到了博山电器社,就是后来的电器制修厂、山东潜水电泵厂。张博伦进入电器社,是他命中注定的归宿,所谓龙归渊、凤还巢。

青年时期的张博伦
这个电器社虽然员工不多,却奇迹般聚集着大量的民间音乐爱好者,水平参差却是同好,叫张博伦好不暗暗惊喜。他很高兴给工人教唱歌曲,工人也都喜欢他,后来这些人都是跟张博伦学的乐器。吹笛子的有胡国华,捧笙的有郭福泉,拉二胡、小提琴的有王茂新、张光一、尚庆丰,拉板胡的有王业春,后来又有弹琵琶的王春蛟、拉二胡、小提琴、大提琴的赵玉福,赵玉福中学时代即拉二胡, 分配到电器社实习,还没入厂就有同学向张博伦推荐说来了个拉二胡的学生。一进厂报到,他就主动找上赵玉福,介绍厂里的小乐队,说咱们厂拉二胡的人多,缺少弹拨乐器,让他改弹拨乐器。后来弹三弦、拉小提琴、拉大提琴、拉革胡都是跟张博伦学的。此时的张博伦以如鱼得水来形容毫不为过。从来都是知音难觅,而这里弹丸之地却是处处知音。跳舞的也有,唱歌的也有。有一位女声独唱演员,在淄博市工人文化宫演出,唱罢掌声雷动,没准备返场节目,报幕员下不了台,只好说:“为人民服务,再唱一遍!”又原歌曲唱了一遍。事实上,工人音乐家们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自学成才,遇到瓶颈往往无力解决,苦于找不到老师。张博伦的到来,成了大家伙的音乐教父,人们聚拢在他的周围,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张博伦也沉醉他的音乐之中。午饭时间,厂区大喇叭响彻革命样板戏的旋律,他从食堂打上菜,端着碗,一边走一边眯着眼哼哼,咣当一声碰到树上,菜洒了个精光,哈哈一笑,比吃了还香。
到了六十年代末,张博伦在博山音乐届已是赫赫有名,这个三十来岁又干又瘦的音乐奇才作曲、演奏、制琴、指挥通吃,把一个小小电器社搞得风生水起,俨然另一个没有编制的文化馆,惹得文化馆馆长、副馆长老往电器社跑,张博伦并不待见他们。
四
时间进入七十年代初,企业更名博山电器制修厂,厂里来了一个专职副书记孙其顺,此前在博城公社分管共青团工作,活力四射,办事干练,风趣幽默,极富音乐细胞。一进厂,就发现这里非同一般,他找到张博伦,请他牵头成立文艺宣传队,大家一呼百应,十几人的乐队立马成立。
当时正是文革中期,文艺宣传工作多而物质却相当匮乏,加上计划经济,稍微上点档次的乐器买不起、买不到。张博伦脑洞大开,向领导提议,买不来乐器咱自己造!张博伦的提议得到了孙书记的支持,孙书记亲自请来细木匠逯维泉,腾出一间屋子专做乐器,张博伦说,逯维泉做,一做做了好几个月,借了博山陶瓷厂的三排码扬琴(这个时期,博陶文艺宣传队也在排练节目,扬琴是不能出借的。打扬琴的是张博伦的学生,很为难。最后想一妙招,请假一天不上班,扬琴就没人打了。他们偷偷拉到厂里量了尺寸、画了图纸)、博山水泥厂的革胡(就是改革了的民族乐器大低音二胡,当时在中国刚刚出现)比着做。转调四排码大扬琴于六十年代研制成功,又称“401型扬琴”,扬琴的调音器托板承受压力大得用硬木,孙启顺跑到委托部花8块钱买来一根很粗的擀面杖,红木的,锯开使上。锯都不好锯,比铁还硬的感觉。先后做成了四排码扬琴和革胡。当时中国民乐界有人对于使用西洋低音乐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提出反对意见,中央民族乐团带头改革,用大阮加上腿进行改造,与大提琴一个拉法,作为大提琴。革胡呢?是在贝斯的基础上洋为中用,用一个加大了的二胡样的鼓子,蒙上皮子,弄一根贝斯的杆子,跟贝斯一个拉法。革胡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没有低音乐器这一问题。买不到贝斯弦,就使用大阮的弦代替,大阮是弹拨乐,和拉弦乐器的弦不一样,关系不准,拉奏很费劲。扬琴做好了,是没有过的四排码,还是转调扬琴。除了使扬琴结构得以简化,将原来只有两组音域的小扬琴,扩大为四个八度,并采用新的音位和码子排列,能够在演奏中做到迅速转调。
扬琴有了,得有琴弦。杨琴弦分多少号多少号钢丝,一买就是一盘。低音区的弦是颤弦,如小提琴一弦是钢丝,二弦三弦四弦都是颤弦,钢丝以外缠上东西。正常扬琴是三排码,琴弦也正常供应,他们制造的四排码,增加了低音区,低音弦买不到,张博伦就用中音琴弦做低音弦。缠啥?是缠漆包线还是裸铜线?缠多粗的?粗了细了不是不准就是不响。最后研究的结果是在钢丝上先缠棉花再缠更细的琴弦。他在家里把琴弦两头拉起来固定住,先缠上一层棉花,再用细琴弦一圈一圈将棉线包好,费了很大工夫以后终于缠出一条低音弦来,放到琴上拿校音器一校,不是高了就是低了。拆了再缠,为了获得音准适合的几根弦,张博伦不知缠了拆、拆了缠多少遍,弄一条就若干天,也不知费了多少个夜晚,总算把低音弦鼓捣成了。他对琴锤有专门研究,软了不行硬了不行,他把在买来的琴锤与琴弦的接触面上粘了绒布,打的过程中绒布容易脱落且声音效果不好,他用钢笔的墨水胆套在上面,即牢固又提高了音响质量。砸到激情处翻过琴锤拨弦演奏,表现力奇强。他还油炸过小提琴码子。小提琴声音没有穿透力,原因归结到码子上,码子的木质内部有空气,怎么办?社会上有人尝试用油炸,把里头的空气逼出来,油来填充。张博伦开始试验,用花生油炸,用蓖麻油炸,最终说明此路不通。自制乐器是被逼无奈,有时想买就是买不到。为了去买两把二胡,从厂里给大街宋家胡同口乐器商店的老王家拉去一地排车炭。

五
张博伦在新村平房里住的是两间小屋,各12平方,母亲一间,自家一间。张博伦的家里,每天晚上都像是赶大集,多的时候得十来个人,从下班,到夜间12点,都是各种乐器的吱嘎声,你来我去的研讨声,每人都是大烟鬼,叼着九分钱一盒最廉价的“勤俭”烟,把小屋子秌得熏煞人。来人都是投奔张博伦的学生,不仅限于自己的工厂,社会上的音乐达人都闻名而来,张博伦来者不拒,他们常常到新庄李同新家里,墙上挂一块小黑板就开讲,每堂课都少不了五六个人,讲乐理,讲和弦,讲配器。那时候也没有学费这一说,连一整盒香烟的酬劳也不必付出,学生们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两支,自己一支,递给老师一支,这就是报酬。
地处新村通往第一医院甬道一侧平房里的那间小屋,笛子响了提琴响,叮叮当当一个晚上,邻居家就没有一个说个不的,大家用非常少见的宽容接纳着这个躁动的存在。峨眉新村东村的男女老少,无一不用好奇的阳光打量,这个干枯瘦小的男子身上,竟然有着如此大的魔力。
毕玉奇1966年从赵家后门搬到新村居住,卖了小时候的一对猪精镇静银镯,卖了一块多钱,化七角多钱买了杆笛子开始吹。那时还小,听说张博伦笛子吹得好,经常跑到张博伦家的窗户底下听他吹。有一天天要下雨,张博伦起来关窗户,一看窗户底下还站着一个小孩,就问,你站在这干啥?毕玉奇说,我来听你吹笛子!进来吧,来屋里,下雨了,别淋着!屋里就有王平远、万盛祥、刘同瑞,后来还有李昌敏。李昌敏去的时候一进新村就开始吹,《小八路勇闯封锁线》。从此,毕玉奇成了这里的一个成员。
毕玉奇特纳闷,张博伦吹的笛子,白白的也不怎么受看,声音怎么会那么水灵?张博伦说,你吹吹。一把小笛子,A调,不是很大,苏州民族乐器厂出品。毕玉奇一吹,“哕!”这个好听法?酥,忒好听了!“是啊,和喝了蜜似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往笛子里装上盐,用布把两头堵上,放进大锅里蒸。蒸后的笛子饱含水分,总是保持湿润,啥时候吹都是水淋淋的。这个时候,张博伦创作出了笛子独奏曲《仙鹤舞曲》,胡国华的弟弟胡国平吹得好。张博伦最专业的是笛子,其次是扬琴,手风琴、二胡、小提琴也拉得不错。家里成了一个音乐沙龙,不仅影响了左邻右舍也有人跑来学琴,周围的人潜移默化地增加了音乐细胞。他一吹起笛子,比如高矩(音),连他的母亲也会立即知道是啥调,“娘,你听是啥调?”“不是F调吗!”。他的母亲一直跟着他,张博伦从新村搬到厂宿舍,母亲才去世。
天大热的盛夏,家家不关门窗,乐队也越来越大,在屋里拉琴太扰民了,这支队伍浩浩荡荡跑到峨眉山大马路的路灯底下,在那里继续演奏。毕玉奇清晰地记得有那么一次,他们正吹拉得起劲,从路北头第一医院方向走来一队车人,几个人提溜头耷拉角拉着一架地排车,一边走一边哭,车上卷着一个席筒子,甭问,是第一医院刚刚过气的病人治回去发丧。张博伦说:“停下停下!”这一班人马就停下手里的家什,站起来,一起朝着马路上的地排车,一句话也不说,行注目礼。等人家走远,然后说,“今晚上咱不拉了,就到这里。”
他拉手风琴痴迷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新村通往第一医院甬道的中段电线杆下拉练习曲,那个地方很阴,文化宫展览馆的后墙上有个窟窿,医院里夭折的小孩不愿意往家弄,走到这里就手塞进窟窿里,成了垃圾。小提琴,多拉《新疆之春》《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选段,一遍一遍拉。笛子吹《小八路勇闯封锁线》,降B调,别扭,吹出来却好听。毕玉奇听来,双吐、单吐,那叫一个天籁之音。毕玉奇注意过他的眼神,总是发空,答非所问,老是深陷在他的旋律当中。他另一个状态是呼呼地喘不上气来。张博伦住到厂里以后,见面少了。一次相遇在东关,张博伦老远见了毕玉奇就跑过来:“听说你写开毛笔字了?好,比拉胡琴强!”毕玉奇说,他与张博伦接触不算很多,但他身上的专注、痴迷、执着,使自己终生受益,他每时每刻生活在音乐中,从来没听说他拉家常,吃啥、穿啥,巴嘴就是音乐!如此说来,他不但是一个作曲家,还是个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器乐改革家,民间乡野的。

李同新的建议采访提纲
六
1974年,迎来了张博伦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由他领衔的厂宣传队代表工业一局参加博山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文艺创作汇演”,厂宣传队推荐8人参加。因为是创作汇演,张博伦的创作曲目大放异彩,其制作的扬琴、革胡都派上了用场,一时轰动博山区。他还搞了个笛子协奏曲,扬琴、二胡、琵琶等民乐伴奏。写出协奏曲不容易,要有若干声部,得有总谱。这个时期,张博伦创作了扬琴协奏曲《草原新牧民》,9/8、6/8、7/8的拍子都有,巧妙地表现了草原风光和牧民生活的意景。民族乐器的扬琴用提琴协奏。是一种创新。扬琴协奏曲《草原新牧民》,代表了他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在淄博工人文化宫剧场一上演,轰动了淄博市,淄博舞台上从未有过,文工团的乐手们都跑来看。这个曲目和他创作的女声小合唱《东北民歌》参加了淄博市文艺创作调演。
扬琴协奏曲《草原新牧民》,除了本厂的乐手,还荟萃了博山所有的小提琴手十几位,比如淄博一中的宋艳玲,是青岛董牧师的学生。出身于基督教世家的董吉亭人称董牧师,一生教了十个学生,宋艳玲是最后一名,其中就有青岛籍小提琴家吕思清的父亲。宋艳玲在博山不教学生,故博山拉小提琴的基本都师从张博伦。当时博山搞音乐的邹大柱都靠在张博伦这边,包括山东机器厂的刘同谋、邹大柱大提琴、手风琴拉得相当好,邹大柱后来是博山水泵厂子弟学校校长。很多弟子学到一定水平再转师淄博市京剧团的赵有斌(后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邓宾雁(淄博市歌舞团小提琴首席)。也有介绍到中央音乐学院正经毕业的学生黄念祖那里去继续深造。张博伦的妹妹张博爱就跟着哥哥打扬琴。学成之后,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宣传队来博山演出,离开博山时全副军装,博山人民夹道送行,十八岁的张博爱一看他们的节目那么丰富,派头那么威武,就报名跟去了建设兵团,打扬琴。到了地界,甘肃农垦西湖农场,再走一步就是新疆,才知道西北是个荒凉之地,住帐篷,地窝子,吃不上蔬菜,见顿洋芋果腹,那是1965年。
张博伦曾创作过乐曲《春耕忙》,文工团的专家说,“春耕忙”没有阶级性,得改成“革命战士春耕忙”。新建二路小学陈同刚老师排练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王福银饰小庞。张博伦的舅舅金其昌在那里当老师,辗转邀请电器社宣传队乐队为他们西乐伴奏。博山后峪小学丁健民老师排了一出《白毛女》,也请他给组织乐队。赵玉福说,那时候没有报酬,也不管饭,全凭一种兴趣爱好去给人家伴奏。演《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一人俩东关火烧当夜餐。陈老师说知道这火烧咋来的不?这是红小兵们拾金不昧上交老师的零钱、粮票买的。当时博山舞台上出现西洋乐,简直是惊人。虽然都是弦乐。第一医院的子弟、后来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付义光买过一只小号来博山区工业局宣传队吹,120块钱,是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铜管、木管单什么的根本买不起,想都甭想。区工会成立宣传队,得知青岛市歌舞团处理旧乐器,派张博伦前去买了两把德国小提琴,一把二百八十元,一把三百二十元,领导说哎呀啊咱叫人坑了,一张三元腿大床才二百四十元。
张博伦是个称职的劳动者,业余时间痴迷音乐,工作起来是拼命三郎,每年都是生产标兵,虽然体重仅有七十多斤。赵玉福说,张博伦每有新曲目问世,都是先拿到车间里,“伙计们,我唱唱你们听听,好不好听。”他就哼唱,工友们听出了这是骑马,那是开车,他就高兴,那是音乐的表达。如果工友们说,“这是捣鼓些啥?听不懂。”他就回家再改,真有点当年聂耳的意思。聂耳当年,创作了曲子不找作曲家、评论家,就找老百姓来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淄博三中王章老师带着学生来厂实习,即兴写成歌词,张博伦马上就谱出曲子,在车间里传唱。在工厂,他是生产骨干,往潜水电机定子里嵌漆包线,定额一个班一个人嵌五台,他能嵌七八台,他写的曲子有了好评,一高兴,能嵌到十台。也没有人骂他,看说你来撑劲,干那么多,领导把定额给咱长上去咋弄?他就是白黑地干,五点下班,他非得多干一个小时。张博伦以这种加班加点的方式来报答企业、工友们对他的偏爱。有一次早上八点排练,九点他还没到,一家人都在等他,这是咋着?写曲子改曲子弄了一宿,临明天才睡着。
一次,他作曲又熬了一个通宵,困得不行了,再点上一支烟,烟在燃烧,他却迷糊过去了,烟头点着了被子,起了火,才把他烧起来。不分昼夜的作曲,一天三包烟的嗜好,糟蹋了自己的气管和肺,胸闷气短到濒临窒息,不得已把烟掐掉,咳嗽差了接着又把烟点上。
七
1976年夏天某日,李同新上头班。快下班的时候有人捎来话,说下了班去保健站给张博伦拿点止疼药,他肚子疼得没上班。李同新把药送到家,张博伦脸色蜡黄,这是为啥?肚子疼还能疼成这样?张博伦说,上午去第一医院看了,人家叫我住院做手术。啥病?咋还肚子疼就做手术?说是慢性阑尾炎,应该吃点药就行。李同新说,要是阑尾炎,光吃药恐怕不行,会格外厉害了。张博伦说,我若住了院,老母亲谁管?从在新村住平房,到住进厂宿舍,他一直把老母亲带在身边。他不肯住院,就想开点止疼药吃吃缓解了,不想疼得越来越厉害。李同新说不行,得赶紧去医院,该住院就住院。
下午三点多,到了医院门诊,大夫劈头盖脸就撸上了:“擦,你还回来做啥?你不是说啥不住吗?你是个啥人这么犟?早上要是住上院不会疼成这样!”李同新说,赶快给他办手续吧!办完住院手续,马上就推进了手术室,本来一个小手术整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做完了天都黑了。从手术室出来,大夫说:“你看他还待不做来,再不做完了他了!”割出来的阑尾全是黑的,上头满是窟窿,实际上肚子里已经满了脓了。
李同新帮着护士把张博伦推回大病房,他还醒着,一会就啥也不知道了,李同新一看,他脸色憋得通红,嘴唇干得纸白,李同新伸手一试,烫手,不敢摸,忙不迭地喊大夫。护士过来看看,用白瓷碗端来一碗酒精,全身擦,物理降温,叫李同新用湿毛巾把水淋到他的头上,不让喝水,只能用湿毛巾擦拭嘴唇。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找人,李同新饿得肚子直叫,又走不开,瘪着肚子护理了一夜。第二天,厂里知道了消息,才安排一个工友过来,与李同新俩人倒班。住着院,都知道病房住着一个作曲家,医院让张博伦为医院宣传队写曲,张博伦都给完成。出院了,邪门的是那手术是某厂医院的实习大夫做的,术后成了肠粘连,并发肠梗阻,伤口两年没愈合,肚子疼像一个撵不走的瘟神,与张博伦形影相随。
八
许多人都听说过张博伦的初恋。有一个本厂的姑娘,宣传队舞蹈演员,不是一般漂亮,欣赏张博伦的才华,一来二去有了感情,确定了恋爱关系,最后商定了订婚的日子。老母亲把彩礼都准备好了,那姑娘却又移情他人,抛下了张博伦。张博伦跑了。厂里派出大量人马去找,最后从白石洞找回他来,差点就寻了短见。
他是一根筋的人,用情专一,受伤也大,发誓再不谈恋爱。姑娘的新恋人也爱好音乐,过去也常在张博伦家里走动,一番花言巧语便撬动了姑娘的初心。能说会道总不顶饭吃,姑娘最后想回头,无奈张博伦关紧了感情的闸门。以后的日子,张博伦经常与疾病做斗争,一年总要住好几次院。企业经济萧条,职工的医药费报不出来,而张博伦每年总有几万元的住院费实报实销,这不能不说是企业领导的偏爱和张博伦的为人。在后来的潜水电泵厂,工厂的工友超越了年龄的界限,不喊张博伦张老师、张师傅,一律称呼他博伦,这里头有对他人格的尊重,更有对艺术的敬畏。一次,张博伦病了,他的初恋来看他,带了两个水果罐头。姑娘走了,他把罐头收拾到厨子里,舍不得吃,断不了拿出来,放在嘴上,闻闻,这两个罐头直到过期变质也没打开。
四五十岁的张博伦历尽了沧桑。老母亲着急啊!怎么还不赶紧成个人家!八十年代初的某个春节,人们换着串门拜年,李同新去张博伦家拜年,张博伦的母亲还托付大家帮着博伦找个媳妇。张博伦去李同新家拜年,同新母亲还劝张博伦早点成个家。过了年一上班,一个消息在厂里传开了:张博伦结婚了!李同新不信,一下班就跑到张博伦家问个究竟。原来传言不虚。
就是那个大年初一,某某厂来了一个拜年的,给博伦介绍了本厂的一个老姑娘,博伦竟答应了,接着就领了结婚证。是那个时代里绝无仅有的闪婚。原来那女的有过两次感情经历,第一个无疾而终,第二个男的占了便宜也发现了卯窍始乱终弃,女的精神乱了。第三次与张博伦结为夫妻,喜不自支,旧病复发,走到北岭村大水池子时一跃跳了进去。张博伦看着不对,又想不出什么办法解脱,一闪身再次离家出走。厂里又派人外出找他,没找着。一天晚上,厂领导韩其诰组织部分职工在赵玉福家商量事,咋着才能赶紧找着张博伦。这时有人敲门,门推开,是张博伦,张博伦也看见了一屋人,倒头就跑,赶紧撵上才把他拽回来,大家都劝他往开了想,他犹豫再三答应去办理离婚,却碰壁而归,答复是在精神病人患病期间不得离婚!最后由工厂出面,罚了张博伦一百八十元钱才给予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张博伦哀大莫如心死,在感情一事上再不越雷池半步。厂领导对他生活上的关照,使他无比感动,怎样才能报答这份情义,他就多干活,每天都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精神错乱的前妻回了原厂,住在后门卫跟前一个小屋,生下一个娃娃,那年冬天,屋里只有小娃娃在床,火炉子点着了床单,床单点着了被窝,小娃娃被烧死,大人被送进了洪山精神病院。
九十年代后期,张博伦的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不会做饭的他只能凑付着吃,偶尔上街买一回菜,从厂区往宿舍有个陡坡,喘不动气,二十米的坡要歇三次。谁若碰上会赶紧说,“博伦,我帮你提!”日复一日,他贫病交加,一日不济一日,终于病退在家。他的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厂里拨给保健站的药费日渐减少,职工在外就医的钱长时间报不了销。寥寥的工资,有吃饭的钱就没了吃药的钱,吃了药就没了吃饭的钱。几个好友看不下去,就找到工会反映,最后号召职工给他捐款。工友们听说为张博伦捐款都很踊跃,三块五块的,十块八块的,厂长高乃祥最高二十块,而那些工友中的琴友们则背地后再多拿三十块。
九
2000年大年二十九,工厂虽说还在上班,但心思都在忙年。像往常一样,他的徒弟王凯明去家里看他,砸不开门,慌了神,唰唰跑到保卫科,胡国华已是保卫科科长,说赶紧走,再去砸,还是没有动静,胡国华说坏了,麻烦了,没法弄咱跳墙吧!好在张博伦住一楼,他们从墙头跳进一楼的后院,从窗户玻璃里朝里一望,昏暗的房间里,靠床一只单人沙发,沙发上缩缩着张博伦,叫不醒,喊不应。他们砸开一块玻璃,伸进手拨开后门,闯进屋内,只见张博伦浑身冰凉,两眼浑浊,奄奄一息,“咋着?咋着?”胡国华使劲喊,怎么叫也不答应。紧急找车把他送到第一医院,熬过了大年三十,到了正月初一早上,山城里正鞭炮齐鸣,不到六十岁的张博伦静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张博伦短暂的存在,影响了六七十年代以后淄博音乐届的生态,他培养了淄博市文工团的首席笛子演奏员刘玉海,弟子翟如生后来也进了淄博市文工团,刘玉海、王东升又教了无数徒弟,刘玉海、王东升的徒弟又教了无数徒弟。他教出了一大批业余音乐选手整整半个世纪活跃在民间艺术平台上。
张博伦去世十五年以后,当年那个经常在他的窗户底下偷听笛子的毕玉奇,陆续完成了《乡籁》《琉璃》《陶瓷》三个系列的民乐组曲,并由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为社会贡献出一个感人至深的“当代阿炳”,用音乐向世界发出了来自博山的声音。

作者与胡辰昌、张博爱夫妇 赵玉福/摄
(图片提供/胡辰昌、张博爱 翻拍/赵玉福)


本文为刘培国先生原创文字
若需转载请联系此公众号
未经授权转载者
将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转发时切勿删除版权信息
刘培国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2976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