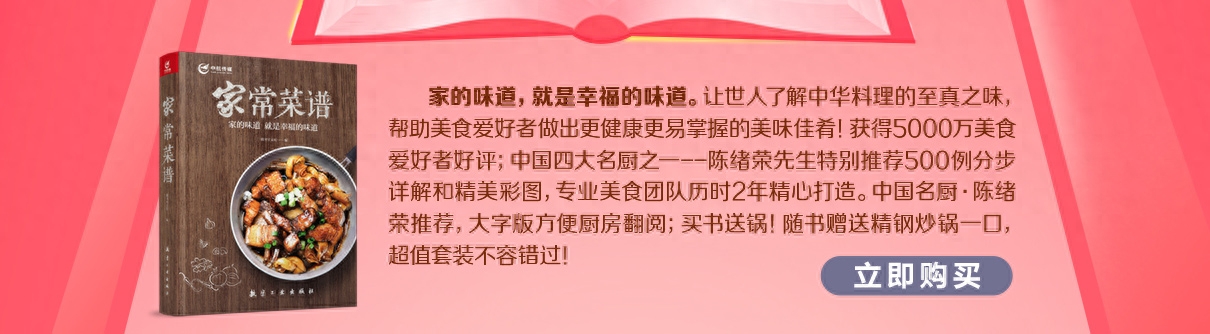石湖的“八碗八碟”
石湖的“八碗八碟”
□张超彦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不能马虎。”夏丏尊老先生的话用在石湖人置办正规酒席的态度上倒也不算偏颇。作为正规酒席的石湖的“八碗八碟”,通常用于红白喜事酬谢来宾,也用于正式的宴请。设宴的目的如此高端,当然不能“杯盘草草”,必须隆重,必须讲究。我们那儿把吃酒席叫坐桌子,让人联想到大老爷坐堂时的形象——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来宾是如此郑重其事,主家更不敢怠慢。

先说说“八碗”。
“八碗”的制作有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模式:统一原料,统一烹饪技法,统一上菜流程,就连每一道菜的主料辅料用量也基本统一。即便在贫穷的七十年代初,这“四统一”也没有改变过。
“八碗”按上菜顺序依次为:鸡子烧黄花菜(在特殊时期,买不到鸡,也曾用瘦猪肉代替,菜名也改为“瘦肉充鸡”,以表达主人的歉意)、烧皮肚、烧肉团子、烧乌子、红烧肉、浪蛋、红烧鱼、菜汤。
把光鸡、五花肉等洗净放到大锅里,添足水,架上火,烧开后转小火,给食物的嬗变留足时间。光鸡烀熟捞出,拆下鸡肉,留着烧黄花菜。五花肉煮熟了,切成大块,留待红烧。一锅高汤熬好,厨师心里有底了:今天这场戏不会荒腔走板了。
肉团子绝对是八碗里的扛把子,它甚至可以作为酒席的代称,吃酒席也被称为“吃肉团子”。“肉团子”,听起来土里土气,没有“狮子头”霸气,也没有“肉丸子”秀气,但绝对形象通俗。
剁团子的声音宣告菜肴的制作正式开始。八大碗的标准模式让厨师的手艺高下立判,因而促进了厨师们的竞争。食客们对厨师的评价,往往先看他做的肉团子好不好吃。面对众多高水平的大众评委,厨师们压力山大。为了证明自己是专业人士,敬业的大厨从挑肉剁肉开始就自己上手。选好了腿子肉,有时还要根据情况加点五花。那时还没有用上绞肉机,全靠人工剁肉。只见大厨围着围裙,两手各持一把菜刀,在砧板上有板有眼左一刀右一刀交替地剁着。那份胸有成竹,气定神闲,让人对他做的肉团子多了一份期待。
石湖街的严大厨在做肉团子上拜过名师,深得个中三昧。他在剁肉的时候把肥瘦分开,先把瘦肉切成小块,再粗粗剁碎。肥肉被他切成“苍蝇头”大小,更费功夫。剁切好的肥瘦肉充分混合,加入他认为分量合适的调料淀粉等,再搅拌上劲,抟成一个个小乒乓球,放入油锅中炸。不必炸熟,外结硬壳就捞出。炸好的肉团子放到调好味的宽汤中用小火慢慢炖煮几个小时。烧透后的肉团子松而不散,滋味浓厚,入口可化,深受食客喜爱。严大厨也因“肉团子”而成名,人称“严大团子”。
石湖酒席上的肉团子是用纯肉做的,不掺入其他食材。自家过年过节时做肉团子,为了让一家人解馋,可尽情地加萝卜、加山药、加白菜、加饼屑……但在酒席上吃肉团子,吃一回就得像一回,吃一个得像一个,这才是待客的样子。
当年坐桌席用的是八仙桌,一桌坐八个人。烧肉团子上来了,没人分配,但每个人只吃三只,这是老规矩,“馒头有数客有数”。碗里会多出一到两只,大家都明白,那是用来压碗的,谁也不会去碰它。

石湖“八碗”当中,最有特色的一碗就是“浪蛋”,这个“浪”很可能是别字,我至今还不能确定究竟该用哪个字。说它最有特色,是因为这道用鸡蛋演绎出来的美味,我还从来没在别处吃过,也没有在哪一部菜谱当中发现过。平桥豆腐因乾隆的赞美而闻名于世,可惜他没口福,没尝过这道“浪蛋”,不然他一定会来一句“佃湖浪蛋,味道好极了”。
这道菜的来历在石湖有这样的传说:有个自称是巡抚大人家大厨的人说自己因为得罪了大管家,被逐出府门,流落到佃湖街豪绅兼盐商薛举人家里。薛举人为了试一下他的本事,让他做几道菜。这碗蛋羹是他做的最后一道菜。他舀了一勺用鸡、鸭、蹄膀、火腿熬煮一夜制成的清汤,又在清汤里打上几颗鸡蛋,配上蟹黄、海参丁、虾仁等,搅搅倒到锅里,叫烧火的烧烧停停,他在锅里拨来拨去。别的厨师虽没看过这种做法,但也不以为然,心想几个鸡蛋你还能做出花来。不料薛举人品尝后,连声叫绝,说一入口便觉胜却无数美味,从此将此菜作为薛府的保留菜品。
后来这道菜流传到佃湖街上,成了各个饭店最受顾客欢迎的菜。
浪蛋是这样制作的:把鸡蛋打入高汤,加盐、胡椒粉,充分搅打,让蛋液和高汤完全融合。锅里烧热,加点熟猪油润锅,倒入蛋和高汤的混合液,用文火慢燎锅底,蛋液在锅壁慢慢凝固。待凝了一层,用锅铲轻轻把凝好的蛋从锅壁分离,再凝再分,反反复复。其间,要不断加入熟猪油润锅。熟猪油点醒了这碗蛋羹的灵魂,在熟猪油的反复滋润下,蛋香愈发醇厚。等到锅壁再无蛋液可凝,打入薄芡,大功告成。
在这道菜的制作过程中,鸡蛋和高汤先合后分,在熟猪油和文火的加持下,原本普普通通的食材完成了华丽变身。因为芡汁的加入,蛋液凝固后悬浮在高汤中,清清爽爽,与高汤若即若离。
做好这碗蛋羹并不容易,它最能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足,汤色混沌,没有卖相;火候过大,又失去了细嫩顺滑的口感。
大厨把蛋羹盛到蓝花台碗(汤碗)里,上菜的人早有默契,撮点青蒜花撒在碗里,再用葱叶蘸着香油甩上几滴,赶紧端上桌去。
只见灿黄的鸡蛋羹上面点缀着几粒绿白相间的青蒜花,色泽鲜亮,小磨麻油的香味在空气中散逸,飘向鼻孔,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引人垂涎。

望着这碗蛋羹,桌席上的老江湖便说:“望屋梁”菜上来了。
促狭的长辈开始戏弄初上桌面的雏儿,作势拿起调羹:来来来,喝喝喝,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自己却不动手,别人也不动声色。雏儿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和长辈的“盛情”,早忘了来时家里长辈的嘱告,舀一勺呼嗤一口送到嘴里,烫得他直吐舌头,连吸几口凉气。促狭的长辈拍手大笑:“哇哇哇,七路桁条三块笆。”过去农村起脊的平房,山尖和大梁上横着七路桁条,上面覆三块用芦苇编的篱笆,最上面苫草或瓦。这句话和“望屋梁”都是描绘被烫者伸舌仰头两眼上翻的窘态的。旁观者也哄笑起来,酒桌上充满快活的空气。
这蛋羹很像一丛带刺的玫瑰,含苞待放,鲜艳欲滴,让人不能自控,看到就想采上一朵,一不留神,小手就被刺出了几滴血珠。
当然,这样的故事一般发生在喜宴上。闹过以后,蛋羹也可以入口了,满桌人拿起调羹,舀一勺热乎乎的蛋羹,小心地送进嘴里,软软的,嫩嫩的,一路滑下肚去,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会舒服地吟唱。一大碗蛋羹很快见底,全桌人都沉静下来,似乎还在回味刚才那份温婉细腻。
当年,很多本土美食家喝了邹姓小厨师做的“浪蛋”,赞不绝口,说他一定得了真传。
红烧肉,是用五花肉烧制的。过去的土猪肉肉白很厚,红烧出来,夹在筷子上颤颤悠悠,很是诱人。当时,我的嗓子很矫情,容不得一颗米粒大的肥肉下肚,红烧肉和我无缘。可奇怪的是,尽管桌上坐着几位平时号称一人可干掉一碗红烧肉的客人,但这碗菜常常是一桌上剩得最多的。后来我才明白,客人们是在用矜持维护着礼仪和自尊。等到我的嗓子不再矫情,我才感受到反复回锅的红烧肉的致命诱惑:浓郁的酱香在唇齿之间荡漾,丰腴不腻的口感给了人无限遐想。

八大碗中唯一的一道海鲜是烧乌子。乌子烧前要浸泡,搓洗,去除不能食用的部分,再撕成碎条,配上时蔬,萝卜丝、菠菜、韭菜等等,什么应时选什么,还要加点蛋皮丝。海鲜、鸡蛋和蔬菜的完美组合,融汇成这碗平民化的美味。
鸡鱼肉蛋,山珍(黄花菜即金针菜,是“四大素山珍”之一)海味,新鲜时蔬,这已是食物匮乏时代倾力准备的最好食材。食材的选择体现了石湖人待客的满满诚意。
烹饪时,厨师们注重保持食物本味,讲究火工、擅长炖焖,口味清淡鲜美、甜咸适中,走的是淮扬菜的路子。

再说说“八碟”。
“八碟”是冷菜,相对于“八碗”,就随意多了。咸鸭蛋是“八碟”里的头牌,必不可少,其它的可以因时取材,原则是保证四荤四素。常用的荤菜还有猪头肉、卤猪耳、卤猪肝、皮蛋等。素菜取材更广,煮花生、煮黄豆,炝萝卜丝、凉拌芫荽,石湖有果园,削个桃子、削个苹果梨子切成小块,再加点白糖也可以算一碟。如果碰到供销社处理临期罐头,也可以买点回来凑一样。
“八碟”当中最重要的是“鸭蛋盘子”。两只咸鸭蛋先对半剖开,再一分为二,变成均匀的八瓣,蛋白像白玉凝脂,蛋黄如红橘流丹,呈花瓣状,卧在盘中,这就是“著名”的“鸭蛋盘子”。说它著名,绝非夸张。它在我们老家的传统酒席上地位显赫,是最重要的冷碟。它要摆在第一席位上,是主宾身份的标志,由主宾专享。人们常通过“鸭蛋盘子是谁坐的”来推断主宾和主人的关系。主宾当然也不会没眼色,会把咸鸭蛋搛给每个人,分而食之。

石湖的“八碗八碟”不知始于何时,在石湖一直流行到上世纪八十代末,后来逐渐式微。可惜的是,石湖“八碗八碟”仅仅流行在石湖街上街下方圆几公里的地域内,没有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佃湖蛋羹”——“浪蛋”的制作方法如果失传将是一件憾事。
说不尽石湖“八大碗”,道不完酒席上的故事。
石湖“八大碗”,值得永远回味!


张超彦,涟水人,长期在乡镇中学工作,喜阅读,爱摄影。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每天跟着我们读更多的书]
互推传媒文章转载自第三方或本站原创生产,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如有内容如侵犯了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fwlcm.com/info/110906.html